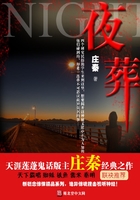李觉爬了好几棵树。李觉爬起树来就像一只矫健的长尾黑叶猴,上上下下很灵敏。李觉很喜欢爬树,他觉得爬树能让他体验一种进入丛林并且向天空中攀升的感受。他抱住湿润而细腻的树干向上爬去。他的双脚离开了大地,一点一点地接近天空。他在某一处临近天空的地方抬起头来,和天空对视,并且微笑。当然他也可以咯咯地大笑,不过这必须是在爬一棵更高一些的大树的时候。这种向天空中攀升的感觉,就跟在奔跑的时候像一匹马的感觉,游泳的时候像一条鱼的感觉,摔跤的时候像一只黑猩猩的感觉,沉思的时候像一棵三叶草的感觉,做梦的时候像一缕云彩的感觉一样,让李觉为生命的生动和活力而感动。李觉常常是感动着的。李觉喜欢这样的感动。他在这样的感动里永远是快乐的,就像一个赤裸着的孩子。
李觉爬上一棵树,他像一只金胸歌鸲一样晃晃悠悠地攀在树端,用脚往下蹬椰子果儿,那些熟透了的椰子果儿一枚枚滚下来,落满一地。
李觉快乐地喊,捡吧,捡吧。
李觉不知道,他的伙伴们早就跑掉了。
李觉后来才发觉有什么不对劲。他发现树下只剩了一个人了。那个人站在树下,站在黑暗中,仰起头来欣赏地看树上的他,很安静地不说话。
李觉坐在树上说,嘿,你干吗不上来?
黑暗中的那个人仍然不说话,很感兴趣地抬头看他。
李觉让自己坐得更加舒服一些,说,你是不是不会上树?这很简单,你只要像一只猴子那样去做,或者是一只松鼠,或者是一只考拉,你就想象着你是他们,而树就是你的家,你到地上是去串亲戚的,你串门串累了,你得回到家里来,你这么一想,你就会很容易地爬上树来了。
黑暗中的那个人仍然不说话,仍然很感兴趣地仰着头看他。李觉被宽宽地树叶遮挡住了,看不见那个人的脸,但他能看见他把手背上了。
李觉很体谅地说,算了,你要实在上不来就不上吧,你可能是离家太久了,一时回不来,没关系,你就在树下,就在你家的门口,你喝椰子汁儿,你就像在你们自己家里喝水一样,别客气。
黑暗中的那个人还是不动。
李觉说,你干吗不动手?你都到自己家门口了,未必还要别人来请你不成?这你就太没劲了,你把自己弄得像个客人,你是不是觉得地上那些椰子果儿不好?我明白了,这就好办了,你既然上不来,那你真的就是客人,客人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你当然不是豺狼,这岛上没豺狼,再说我刚来,还没发猎枪,要是有豺狼我得空手去套,那就过瘾了,那你就喝酒,上好的椰子酒,我给你新酿一批,咱家管够,你就敞开了猛灌吧。
李觉说着就站起来,一脚一个。椰子果儿像雨点一样往下落,黑暗中的那个人没躲得及,其中一个椰子砸在他的头上,砸得他哎哟一下叫出了声。
李觉蹲在树上。他哧哧地笑了起来。但是他很快不笑了。李觉发现有什么不对。他的听觉很好。他能听出一窝田鼠中两只小田鼠不同的声音。他现在就听出站在树下黑暗中的那个人,那个被椰子果儿砸了脑袋的人,他不是他熟悉的田鼠窝中的一只。李觉哧溜一下抱着树干滑下树来。李觉正打算问你是谁?但李觉没有问。李觉愣在那里了。
李觉借着月光看见那个人的肩牌上顶着光闪闪的两杠四花。
李觉发现,在月光之下,肩牌显得非常的好看,特别是肩花多一点,大一点的时候,那种样子就更加好看了。
连长事后气得差点儿没晕过去。连长打着嗝说,李觉你胆子也太大了,你你你连司令员的脑袋都敢砸呀!
七
海军新兵李觉上岛不到四十八小时就犯了两次错误。
第一次,李觉主动要求做好事,他帮助连长为弟兄们剃头,他没有执行连长一寸二的指示,结果把弟兄们的头全都削成了土豆。
第二次,李觉上树去摘椰子,他把椰子树当成了自己的家,邀请司令员上他的家里去,他说了很多废话,比如猴子、松鼠、考拉,比如客人、豺狼、猎枪,比如串门、亲戚、喝酒,而且他不光是说这些废话,他还用椰子果儿砸司令员。
李觉这样犯错误,他的错误犯得让人啼笑皆非,就难怪要受到狠狠地批评了。
李觉在晚点名的队列讲评时挨了批评,大家都很同情李觉,下来之后,大家都来安慰他。
陈在说,李觉你不是有意要砸司令员的头吧?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你只不过是一时糊涂而已。
赵大国说,李觉你肯定是失误了,你把三分球当篮下球投出去了,你要是真想砸,你非把司令员砸晕过去不可。
林屈说,李觉的关键问题不是糊涂和失误,李觉的关键问题是撤得不够及时,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以致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这恰恰证明了英雄主义的悲剧性。
胡水兵在一旁有点看不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哪里是在真心地帮助李觉同志,完全是在庸俗地吹捧,是要把他高高地挂起来,挂在椰子树上吊着,让他下不来,让他继续蹲在上面用椰子果儿砸人,你们是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亏得你们还自称是他的好朋友,真是可悲复可耻呀!
胡水兵转过头来,很严肃地对李觉说,李觉同志,你不要听这些人这么说,他们这么说,那是害了你,你要头脑清醒,不能上他们的当,你应该充分认识清楚自己的错误,要认清你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表现自我主义、个人逞能主义、骄傲自大主义、神里神经主义、不尊重他人主义,等等等等,你要把你的这些主义认识清楚,你还不能放任自流,不能自暴自弃,不能破罐子破摔,这样你才能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让全国人民放心的海军战士。
陈在吹了一声口哨,吹急了一点,没吹响。陈在说,胡水兵,怎么听你说话的口气有点串味,像是中纪委领导,你什么时候当上领导的?
赵大国说,你也别先急着当领导,在座好几个前任支部委员和学生干部,你先把申请书写了交上来,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再说。
他们在那里说什么,李觉一点也没听见。李觉在那里整理着内务。李觉整理完内务后就去打水洗脸洗脚。熄灯号吹响的时候,李觉已经躺到床上去了,安安静静地,一点也不像是李觉。大家都纷纷手忙脚乱地上床。过了一会儿,连长进来查铺,宿舍里立刻响起一片呼噜声。连长转了一圈,熄了手电走了。又过了一会儿,陈在从床上爬起来,轻手轻脚地溜到李觉的床边,摇了摇李觉说,李觉你没事吧?李觉一点动静也没有。陈在站了一会儿,又轻手轻脚地溜回自己的床上去了。
李觉一直睁着眼躺在那里。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李觉知道他拿椰子果儿砸了司令员的头这是不对的。李觉还知道他不该把伙伴们的头全都削成了土豆。司令员的头不能随便砸,谁的头都不能随便砸,不但不能随便砸,还不能随便削,比如削成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种土豆。这些道理李觉都明白。李觉明白但是李觉没有能够做到,他一连犯了两次错误,他犯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他触犯了一些规矩,而那些规矩是被认定为不能去触犯的。李觉不想触犯什么规矩。李觉不想触犯任何东西。他只是对规矩这种东西有点茫然,有点不习惯。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他老是忍不住要去拥抱它们。他不知道那些东西它们是不是喜欢他的拥抱,他的拥抱会不会把它们弄疼。他总是一相情愿满怀热情地那样去做,结果往往是它们不喜欢,他把它们弄疼了。李觉在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的。他有时候会做梦,会在梦中变成一匹马儿、一道闪电、一粒草子或是一棵树,但这并不说明他就不快乐。如果说李觉有什么不快乐,事情往往就在这里,就在于李觉和那些规矩发生了矛盾,它们不喜欢他的拥抱,他的拥抱弄疼了它们,让它们生气了,它们生气了李觉就很难过,就很沮丧。
李觉现在就很难过和沮丧。
李觉在难过和沮丧中,就想起那条鱼来了。
那条鱼,那条他抵达永兴岛时出现在海里的鱼,它现在在哪儿呢?
李觉一想起那条鱼来就浑身一激灵。
李觉从床上爬起来,蚕蛹入茧一样地套上衣服,轻手轻脚地出了宿舍。
李觉要去寻找那条鱼。
李觉朝岛子的北端走去。那些熟悉的风在他一出现的时候就拥了过来,老朋友似的和他拍脸撞肩,并且大声喧哗,先前它们一直是在岛子上摔跤来着,它们摔得很辛苦,气喘吁吁,至今没能决出胜负。那些美丽的椰子树,它们则躲藏在黑夜中窃窃私语,只是在他走近了的时候,故意背过脸去矜持地不说话,或者装作无意间地用长发和裙裾去拂扫他,而先前它们可是在那里哧哧笑个不停地梳妆着的。有两只鸟儿从天空中飞过,是红嘴蒙鸟或是小军舰鸟,它们像一段被风儿吹散的云一样无声地贴着月光飞过,在银色的沙地上留下一道梦一样的幻影。李觉没有停下来。他脚步匆匆地往前走。他本来可以变成一只白爪灵猫去椰树林中游戏,或者变成一只褐尾鲣鸟去追逐刚刚飞过的那两个同伴。但他没有那么做。他没有看他的那些伙伴。他急匆匆地朝岛子的北端走去。他穿过隔泄湖上长长的栈桥,来到石岛上。
李觉现在站在石岛上了。
李觉站在石岛最北端那一片城堡似的礁石上,他的脚下是漫过来的大海,它在离他最近的那个地方深深地沉了下去,形成了一个深潭,海水在那里是静止不动的,它们在月光下有如一大块睡着了的翡,安静而神秘。李觉看着那个深潭,他的心里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他是对的,他知道它在那里。那条鱼,那条有着美丽的背鳍和鳍肢、嘴儿尖尖,下颌圆圆、大脑沟回复杂、小小的眼睛明亮而纯粹的鱼,它在那里。他朝礁石下走去。他的脚碰到了一枚活泼的紫眼球贝,然后是一枚傲慢的希伯来螺。他站在那里,开始脱去衣服。他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一扇巨大的朴实的鳞砗磲上。他知道那条鱼它会喜欢这样的方式。现在他是赤裸着的了。他赤裸着,闭上了眼睛。月光在那个时候突然一下明亮起来,像海水一样泼洒在他的身上。他是那么的结实,肌肤饱满光滑,四肢修长有力,在月光下就像一块活过来了的礁石。他站在那里,开始感到自己在发生变化,他的两腮在隐隐地作痛,皮肤越来越干燥,哔哔剥剥地生出鳞片来,他的一双腿渐渐地黏合到了一起,背上和两肋间有什么东西正在从那里冒出来。他睁开眼睛,热泪盈眶地朝海里走去。
李觉接触到海水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那条鱼,它和他一样都属于哺乳纲,它和他一样都属于群行类,他们是怎么离开自己的伙伴的呢?
李觉像一条鱼儿似的没入海水之中。
1999年3月1日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