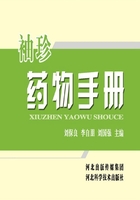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是非常有哲理的。
端端是在他的浅粉色的婴儿车上认识马的。
深秋,正是北方抢购冬储菜的季节,四乡的马车纷纷拥进城里,我和端端的妈妈推着他去菜点看菜,端端看见了马,他在车里几乎把屁股都颠坏了!他睁大眼睛,双手拍着婴儿车的扶栏,一下一下地跳着,惹得周围的人都跑过来看他。
“马!”我告诉他。
他并不理我,自我陶醉在惊喜之中!
端端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我坚信他听懂了我的话,我是那么的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对他说:“马!”
妈妈也是。
端端的妈妈抱起他,指着一匹白马说:“大马。”
我补充说:“拉车的大白马。”
我们一家人笑成一团。
我之所以说端端听懂了我的话,是因为当端端自己能冒话儿以后,最先会说的几个单字里就有马。那已是1990年的春天的事了,我领着他在街边看发芽的小草,他突然指着不远的一棵树下说:“马!”
我抬头望去,是一辆收废品的驴车停在那里。
端端指着毛驴大叫:“马。”
在孩子的认识里,它们太相似了。
我纠正他说:“不是马,是驴。”
他不解地看着我,仍旧固执:“马!”
我无奈地摇头。他太小了,我无法和他讲清马和驴的区别。端端长大之后,我曾和他说起这件事,他大惑不解,连连说我瞎掰,他把后背对着我,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可能,驴跟马根本不一样,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孩子大了,慢慢地就学会和我们分辩。
端端小的时候缺钙,后脑勺特别大。他走路晚,和他差不多一同出生的孩子都会走路了,他却还只能扶着东西站着。端端的妈妈很着急。
“他的骨头是不是软呀?”她问我。
我马上反驳:“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我向她历数端端所创下的奇迹。
那时,端端已经有11个月大。一天,他妈妈正在厨房给他煮奶,我则伏案工作。当我无意间侧转头时,发现刚刚还躺在小床里睡觉的他,竟扶着床帮站了起来。我惊得大叫,端端的妈妈也吓了一跳,我们一同跑到小床前,蹲在地上护着他。好半天,我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端端的妈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个紧紧的拥抱当然缺少不了端端。
我们把他搂在我们的怀里!
其实,我们还是忽视了这件事,端端已经长高了一截,小床的床帮对他来说已不足为护。不久,在端端的又一次站立时,他从小床上跌了下去。情况和上次一样,我在赶抄一篇稿子,妈妈在厨房给他做饭,从端端八个月大时,妈妈已经开始给他做碎米粥吃,妈妈的奶水越来越稀,就特意去市场买来便宜的碎米给端端熬粥吃。
端端妈妈对我说:“我做饭,你看着点孩子。”
我嘴上答应,眼睛却还在稿子上。
端端是什么时候从床上站起来的我不知道,他呀呀地叫着,向前一扑,从床头折了下来。我伸手挡了一下,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我挡一下,但他的头上还是撞出了一个包。
端端妈妈冲进屋来,比我更快地抱起了他。
端端大哭。
他的妈妈埋怨我,而我见孩子无大恙,就自顾傻笑。
我傻笑,心里却有着深深的歉意。
…………
我列举这些例子,不过是想告诉端端的妈妈:端端可以从床上窜到地上,说他的骨头软,鬼才相信呢!
“不软?”妈妈不放心地问我。
“不软!”我使劲拍了拍端端。
又过了一个多月,端端过完一周岁生日,这时,他已经可以像螃蟹一样扶着床头来回走了。他的迈步方式很笨,一点也不灵活,时常把自己绊倒,绊倒了他会很费力地爬起来,之后,又扶着床头“跳舞”。现在想起来,他的“舞”姿有点像南美洲的桑巴舞,急切和零乱之中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美感。
耐人回味。
是时候了。我和端端的妈妈开始教他学步。
我们把大毛毯对折,松松地拦在他的腰上,我和他妈妈一人拉住一边,慢慢地向前徐行,端端的腿脚还是不灵活,不知道向前迈步,有时,我们几乎是拖着他走,他像一只初飞的雏燕,脚尖一会儿着地,一会儿又被我和他妈妈拉起来。
小孩的关节像尚未润滑的新机器。
运转。生活不可阻挡地运转、向前。
在我们的殷殷期望之中,端端终于可以自己迈出胆怯的步伐了!那是他14个月大时,我和他妈妈抱着他去外边玩,我蹲在他的身后,双手虚扶着他的两肋,妈妈在他前边一米远的地方。妈妈冲他拍手,他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他羞涩地笑了,眼睛眯眯地望着妈妈,突然抬起右脚,蹒跚地扑进妈妈的怀抱。
他的两只小手高扬。
他成功了。
他扑进妈妈怀里,头在妈妈腋下拱着。
他踮着小脚前进的样子像一头小小的梅花鹿,像一个不成熟的音符。
端端平衡他走路的倾斜就是举起右手,这个习惯直到他两岁以后才慢慢丢掉。
粗心的父亲也许不会记得,每一个学步的婴儿都是从跑开始的,实际上,他们首先学会了奔跑,然后,才能学会平稳地走路。
或者说,他们首先学会的是不规则的跳越!
对于端端的这一点,我记得那么清晰,如今闭上眼睛,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昨天。
在我的日记里翻查不到有关端端第一次说话的记载,但我对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牢记在心。那是1990年的冬末春初,星期日,我不必早早起床去工作,但我醒得很早,依在床边读书。那个早晨阳光很好。
七点钟的时候,暖阳就已经爬过我们的窗台,爬上端端的脸。我放下手中的书,静静地看他,他的脸上有密密的细细的绒毛。阳光最喜欢和婴孩游戏,我想。我目视着阳光偷偷爬上端端的脸,轻轻地跳跃,抚弄,让他痒,让他从睡梦中醒来。
端端动了一下,并未躲过阳光的偷袭。
又动了一下。
然后,他睁开了眼睛。阳光刺了他一下,他马上叫了起来。
游戏到此结束。
我披衣下地,从小床里抱起他,一夜的足睡使他的身子又温热又柔软。我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肌肤相亲,十分舒服。
这种爱显然让端端非常受用。
他蹬着两只小脚,头努力地后仰——这是端端高兴时的一种表达。
端端看着我,突然冒出一连串他以前从未发出过的音:“拨拨拨拨拨……”
我愣了一下。
然后我猛然明白了。
我不顾一切地推醒端端的妈妈,告诉她这个喜人的消息。她昨夜睡得晚,此时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她迷迷糊糊地坐起身,问我:“怎么了?”
我说:“端端叫我爸爸了!”
她也一下醒来。
“什么?”她从我怀里接过端端。
“端端会叫爸爸了!”我再三重复着。
她马上把脸贴在端端脸上,以示奖励。她摇着端端,对他说:“宝宝会叫爸爸了,给妈妈叫一声听听!”端端可没那么乖巧,他把妈妈的举动误解为和他玩耍,注意力很快就投入进去。
妈妈说:“叫呀,叫爸爸。”
端端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端端的妈妈怀疑地看着我,以为我在寻她开心。可我的神情分明表示这一切不是假的,刚才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就在刚才,端端一连声地叫着:“拨拨拨拨拨……”余音袅袅,还未完全从我的耳廓中散尽。
仅仅在第二天的中午,端端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第二天中午,我回家吃饭。端端的腰上被妈妈系了一个带子,带子的一头系在床头,以防他再次从床上跌到地上。
我进屋,脱下外衣,放在床边。
端端的妈妈跟在我的身后。
这时,端端从床上费力地站起来,向我伸出了双手。他清晰地吐音:“爸——爸!”
两个单音,间隔很长,但那么准确!
妈妈冲过去,一把把他放倒在床上,她高兴地叫着:“没良心的小东西,妈妈天天在家带你,你不先叫妈妈,竟先叫爸爸!没良心的东西,白心疼你了!”
我心底的喜悦油然而生。
那顿午饭,我吃得格外香甜。
端端学会的第二个单音是:“抱!”这也是一种本能吧?
想一想,我真的是很幸运,端端冒出的第一个句子也紧紧和我关联,他说的第一个句子是:“爸爸抱抱!”
爸爸抱抱!
让我如此之深地感受了父子亲情。
时间像流水,无论你多么的匆忙,或者多么的悠闲,它都会在你不经意之中静静地向前流淌。时间的河水,泛着金色的光波。
转眼,端端15个月了。
他长成一个又白又胖惹人喜爱的小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