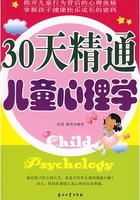年少的时光总是美丽的。
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以古莲子而闻名的小城。据说古莲子是千年遗留下来的一枚种子,一枚不死的化石。
满塘莲花,风吹荷动,清香环绕。莲花的香,比别的花儿不同,淡雅清丽,若有似无。当然,我也喜欢莲花的风骨,出淤泥而不染。远远地望去,波光潋滟,一塘碧萍染绿了半边天,连塘边的垂柳也被熏染得多了几分醉意。
我曾和一群写诗的朋友一起,骑着单车去莲花湾看古莲。那时候可真年轻啊,年轻到没有任何的底色和背景,连“喜欢”这两个字,都是如此纯粹,没有丝毫杂质。我不会写诗,至今都不会,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当一个合格的听众。
那是一个为诗倾倒和狂热的年代,读顾城,读北岛,也读舒婷。至今仍然记得那些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那些句子,我至今记得,和血液一起流动,镶嵌进记忆里。
我们喝啤酒,读别人的诗,写自己的诗。当然,那些诗写得并不怎么样,但却是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是青春的注脚,是快乐的源泉。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却并不影响我们为之狂热和颠倒,因为那些诗句像火把一样点亮了我们的青春,照亮了我们还不曾开始暗淡的人生。
我们读诗赏莲,逃课去电影院看电影。小城很小,骑着单车,半个小时就能把我的小城绕一圈。那家电影院就藏在一个角落里。每天日落时分,夕阳把电影院印成剪影时,我们骑几分钟单车,跑去电影院看看墙上的海报是否换了新的,是不是又上演了新片,那是我们最大热度的关注。
售票的女孩是电影院门口的一个招牌,两个长长的麻花辫,红嘟嘟的嘴唇,齐齐的刘海,比海报上的人儿还漂亮。有留长发、穿喇叭裤的男孩,隔老远对着她吹口哨。她不屑一顾的样子,带着几分轻蔑,很酷。
如果现在要问我对电影院的印象,只怕对那个售票的女孩比对电影院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她红嘟嘟的嘴唇,是那个年代,到处一片灰暗的年代里的一抹亮色。
电影院应该是一处旧厂房改造的,座椅很密很凉。门口挡着厚厚的旧帆布门帘,因为进出的时候,多半都会被人摸一把,因此看上去油腻腻的。我们坐在简陋的座椅上,全身心地、专注地盯着荧幕,眼睛一眨不眨,生怕错过一个细节。看到有拥抱和接吻的镜头,女孩会脸红心跳,男孩会吹口哨,掩饰着窘态。
可惜没多久,电影院就改成了录像厅,里面进进出的,多半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和痞里痞气的男人,满屋乌烟瘴气和一地的瓜子皮。
我们不再去电影院,青春的脚步仿佛一下子停滞不前。青春没有了出口,我们变得像一只只被圈起来的困兽,乏味地骑着单车在小城里东游西逛。对未来没有设想,对青春没有奢望。
后来,我们常常去小城的火车站,因为我们向往远方,我们想坐火车去小城以外的地方,看看天有多大,看看地有多宽。
起因是,邻居家的一个姐姐,跟着恋人私奔了,就是从这个小小的火车站出发的。这件事情让我深受刺激,我忽然对那两根神秘的锃亮的钢轨产生了好奇,因为它一直通向远方,可以让人去想去的地方。
那个小而破败的火车站,快车不停慢车停的火车站,看着那些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人发呆,任时光在墙上慢慢地游移。总想着有一天,我也会像这些人一样,捏着一张属于自己的火车票,去远方。
经年之后,我的青春遗留在了我的小城。我的小城时光,我的仓库一样腐朽的电影院,我的破败而陈旧的火车站,我的乏味而狂热的青春,都永远地滞留在身后。
有人问我:“如果可以选择,你还愿意重过一次那样的时光吗?”
我点点头,又点点头。真我愿意,真的愿意。它们旧照片一样承载着泛黄的时光,因为纯粹而美丽,因为美丽而盛开,盖着青春的邮戳,在记忆中永远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