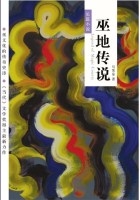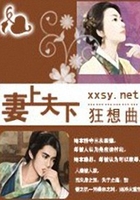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觉得不舒服,睡觉不像睡觉,工作不在状态,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四的下午,到底撑不住,去医院看精神科,医生说我抑郁,开了一星期的药。
从医院回到家,吃了药,终于睡着了,还做了个五彩斑斓的梦。头原本是痛的,从两侧太阳穴到耳朵上方,痛得想撞墙,还怀疑自己中了毒,吃过药十来分钟后,痛像一缕风从耳朵上方飘走了。于是坐在电脑前睡了过去。睡眠缺得离谱,稍放松就睡着了。大概睡了个把小时就醒了过来。腿被压得又麻又痛。去厕所洗脸,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在摇晃,怀疑身处穿越剧,有种悬浮的感觉。低头看脚,又扎扎实实站在地板上。感觉很不真实,怀疑自己肿胀了很多倍,头和身子之外像套了层泡沫,下意识去摸时又落了空。
客厅中的一帆风顺开了三朵白色小花,叶子上落满了灰尘,要拿去洗手间给它冲澡,走到半路,一头撞在墙角,花盆砸在脚面上,痛得要死。花盆没破,泥土洒了一地。走路都在飘,成半仙了。惶恐。继续吃药。药有宁神作用。之后又睡。噩梦连连,醒来时,全身湿透,床单上显出一个人形。
周四晚上,拿了假条上楼给小雪,请她明天带回单位办公室。小雪望一眼假条,抬头看着我说,你果然是有问题。她说她也觉得我这段时间不对,只是不敢相信这么严重了。我说没事,休息几天就能缓过来。医生给我两周病假。小雪跟我同一个集团不同的子单位,我每天坐她的车上下班。
星期五,一早起来头又痛,身体也酸酸痛痛,像运动过量。又吃药。整天都在旋转中清醒着,半梦半醒。不吃药头痛,吃了头晕。我的身体非常敏感,不管什么药,似乎都是副作用更大一些。中午,懒得出去吃饭,甚至不想打电话叫外卖,吃几块饼干,喝一盒李小正的牛奶。
时间过得真慢,从未如此难受过。浑浑噩噩中,觉得生活毫无意义。
下午,太阳从西边的阳台上铺进来,白花花的,晃得眼睛不舒服。
看什么都不顺眼。在家呆不下去了。发短信给老婆:我去深圳走走,你下班后接小正,预计明晚回。
在广州东站走来走去,找不到卖火车票的地方。上个月去深圳办事,来到东站,还像回到自己家中那么自如,现在却像进了迷宫。是因为吃了药的原因还是药吃得不够?
烦躁、焦虑,非常严重。
“大哥,问你个事。”一位白白胖胖的东北大妞在我身后喊。她身后还跟着个黑而瘦的小妞。我喘着气站定。长得像芙蓉的大妞说:“大哥,跟你商量个事。你看,我们在这好几天了……”每回到这里来都会遇到类似的人。真不明白,他们的演技这么粗劣怎么能骗得到钱。我转身就走,芙蓉也跟着我小跑,一边跑还一边嘟哝:“哎哟哟,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一回事,好像姐能吃了你似的!”我看看前面不是卖票的地方,折返,差点跟芙蓉撞个满怀。芙蓉还未吭声,我暴怒,瞪圆双眼吼:“滚!”芙蓉吓了一大跳,却还死撑:“哎哟哟,你看你都急成啥样了。”我恨,挥拳就砸。拳在半空停下来。双方对视了一小会,我从芙蓉身边走掉。走过去后,回头看,见到芙蓉似乎在抹眼泪。
真是变笨了,自动卖票机用过多少回了,这次却不会用,像乡下人似的请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帮忙。好不容易买到了票,又把身份证拉下。还好那貌似学生的人追上来把身份证还给我。这事情虽然不大,但也给了我打击,挫败感又来了,像有个小妖精正在将我的太阳穴当鼓打。
动车的好处是人不多,不好的是太安静,车厢不吸音,如果有人讲话,整个车厢都能听得到。前面的阿姨应该是香港的,从上车开始就在讲电话,貌似在给什么人牵线搭桥,女中音,浑厚,但刺耳,谈话内容拉拉杂杂,鸡零狗碎。往耳朵里塞上耳机,收音机没信号,一片稀里哗拉的杂音,车快得连信号都接收不到。有点杂音跟阿姨的声音对抗,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真想睡觉,但怎么能入睡呢?药是不敢吃了,再吃下去,怕智力受损。
前面的车厢是餐车,正是晚饭时间,味道浓烈得让人直咽口水。饿得快死的感觉,但坚持着不买饭吃。自虐。我越来越喜欢自虐了,似乎。个把小时的车程还搞餐车,居然还有人买,真是奇怪,老子偏不吃。
到了深圳,华灯初上。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回,却还是出了差错。我跟着一个旅游团从一楼的侧门走了出去。出去前我怀疑从这出去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向楼上走,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出去了。旅游团的人出去后被一辆大巴接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傻站着。原本是要上到二楼的平台上去坐车的。出去的地方也有公交车,但车很少,没有我要去的地方的。但我要去哪里呢?我觉得自己有点混乱。
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这才突然想起,我来深圳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在家里呆着烦躁,急急地下楼去了地铁口,去了火车站,再来了深圳。去年也试过这样,周六的早上醒来后倍感无聊,一时心血来潮,坐高铁去了长沙。
在深圳火车站下面绕来绕去折腾了二三十分钟,一直都找不到上二楼平台的路,像遇到鬼打墙,原地打转。停下来抽烟。打电话给深圳的朋友阿森,告诉他我在深圳火车站迷路了。阿森以为我在讲冷笑话。阿森是个文学青年,他的第一个小说是我编辑发表的,所以他总喊我李老师。在深圳,我好意思骚扰的人只有阿森。
阿森弄清楚我的处境后很着急,要赶过来接我。我骗他,说我正准备上一辆的士,让他在公司附近找间餐厅等我,把地址发来给我。
有辆的士在我身旁停下来,但我转身走开了。我跟自己叫上了劲,非要坐公交车过去。去到阿森公司附近下车,阿森的电话打过来,告诉我地址,我上了辆的士过去。
半年没见,阿森变白变胖了。他旁边有个女孩,小小的,瘦瘦的,是他新交的女朋友。
阿森抬头见到我,忽的一声弹起来把我抱着。他那么胖,我以为自己被裹进了一块会走路的海绵。我到底不习惯亲密无间的接触,身体僵硬着。
小女孩一会就走了,说去东莞看她姐姐。我问阿森,这大晚上的,让一个女孩去东莞不担心么?阿森说,坐火车去,一会就到了,出了站打车过姐姐家,比从罗湖去福田还安全。
女孩走了后,阿森盯着我看了好一会才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说我的肉都跑你身上了。阿森让服务员上啤酒,又加了下酒的菜。
两个人喝酒到底是闷。一会,肚子就撑得难受。闷。把剩下的酒退了,埋单走人。阿森要带我去他的出租屋。我说算了吧,你那狗窝,老子不爱去。以前去过他那里,城中村的牵手楼,阴森、潮湿、狭窄。阿森说今时不同往日,鸟枪换炮了。跟他过去,果然是,是小区里的单间。他跟女朋友一起住。人们都在进步,只有我,倒过来活,越混越差,抑郁症都患上了,离发疯只一步之遥。但只有一张床,怎么睡?阿森说他睡地板,我睡床。
洗过澡躺下才几分钟,地板上的阿森就开始打鼻鼾。空调旧了,呼呼地响,与阿森的鼻鼾遥相呼应。我在他的床上折腾,躺一会,坐一会,睡不着,反正是睡不着。一个小时后,我下去推阿森。他估计在做梦,猛地坐起来就喊,什么事,什么事?我说没事,没事,咱换个地方睡。
换了位置,三分钟后,阿森又开始打鼻鼾。我做掌上压,做仰卧起坐。憋气做,怕吵醒了阿森。
强烈地想去酒店住。来阿森家之前,我是打算住酒店的。但这大半夜的,怎么去呢?是偷偷去还是叫醒阿森陪我一块去?阿森待我如兄长、如老师,但我既不是他的兄长,也不是他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