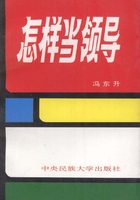沧月
在很多事情上,我好像一贯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如今教师节都已过去了,才来写上这一篇东西,用来追忆二十多年来在我生命里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师长。那些人,是我人生的引导者,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可能随着岁月变迁而荒废或者遗忘,但是作为灵魂的塑造者,他们对我的影响却会贯穿我的毕生岁月。如今他们有些退休了,有些还在职,有些甚至已经过世。
时间和空间都已经远离,但是我还是会时常想起那些成长里的点滴。
生命里的第一个启蒙者当然是父母,这个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而正式的启蒙者,是小学里的语文老师黄老师。因为年代太久远,很多事情已经模糊,只记得老师长得很像当时热播的《血疑》里的男主角三浦友和,八九岁的孩子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审美标准,当时就是以电视上的标准来衡量,觉得:噢,这个老师很帅。
这是第一个教我把字组成词,词组成句,句组成文的人。小学开始我的成绩就很好,但学习书法却并不见得出色。老师很有耐心很温和,很少责骂我,他手把手地教我练习书法,从《神策军碑》到《玄秘塔碑》,记忆里他的模样总是伴随着萦绕的墨香和厚厚的一大叠毛边纸宣纸。虽然花了不少的时间,我的书法却始终不见得出类拔萃,最多在市里拿过三等奖,唯一的收获是通过临摹碑帖识别了大量繁体字,从此看家里那些繁体字竖排本的古籍不再费力。
上大学后,听说黄老师病了,是一种罕见而可怕的病:重症肌无力。症状的最初,只是拿不稳粉笔,渐渐的手足无力,不能走路;再到最后,全身肌肉开始萎缩,等到胸腹肌肉都失去力量后,便会无法说话和呼吸。等我返回家乡去探望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昔年英姿勃勃的老师变得非常消瘦,说话声音微弱,我听不清,却不忍追问他到底说了什么……呃,不想再复述那个场景了,太令人悲伤。
那一次的见面后便是永诀。
如今他的女儿已经从复旦新闻系毕业,非常优秀,也算可以告慰了。
中学的语文老师姓蒋,是一个幽默开朗的人,讲课风趣生动,经常让同学哄堂大笑。在入学的第一次的语文课上,我便令他刮目相看,从此后这个开明的老师允许我在他的课堂上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是看无关的书籍还是写作,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当然,前提是每次语文考试我必须给出满意的分数。
他甚至提出要阅读我偷偷写的那些在大人眼里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小说,而没有责骂或禁止我的涂鸦。不同于坚毅沉稳的黄老师,蒋老师热情洋溢,从不吝惜对我的夸奖,多次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是他从教十几年来遇到的天资最出色的学生,将来必成大器。听说如今他还在母校执教,经常会有学生向他问起我当年就读的事情,而他依然还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早慧的孩子都是骄傲而敏感的,成人世界的一语一行,一个鼓励的眼神或者一个冷漠的拒绝,都可能改变孩子人生的轨迹,而正是这位老师,给予了少年时的我以极大的信心。
那时候的其他一些老师,比如教英语的莫老师、陈校长,都是我成长路上的良师。
我的硕士生导师是卜老师,她是中国建筑学开山四大师之一杨廷宝的关门弟子,浙大建筑学系的系主任,主要研究景观建筑,曾经主持设计了浙江省茶叶博物馆等著名建筑。因为她是出了名的学者型教授,所以我在毕业后报考了她的硕士生,她不像别的“实干型”教授一样老是抓手底下的学生来帮自己干活,这样,我就有时间可以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这是我的小小私心。
虽然大家私下都以“卜妈”来称呼这个慈祥的老太太,但在我眼里,导师始终是一个威严不可亲近的人,两年半来我都有点怕她,每次不得不去她办公室的时候都觉得忐忑不安紧张万分。在毕业论文预答辩的时候,因为准备不充分曾经挨骂,更让我见了她就毛骨悚然,不得不在春节寒假里加班加点地重新写了一遍。正式答辩那天,我前面一位同学几乎被答辩委员会的主持教授给声色俱厉地直接毙了,老师的脸色非常不好,盯着第二个上场的我看,看得我战战兢兢,心想阿弥陀佛老天可保佑我顺利通过不要重修啊。结果……答辩结束,我拿到了那一届老师那批学生里唯一的一个优等。
很奇怪,在读书的几年里,我一直非常畏惧和退避着我的教授,但毕业后,我却和老师建立起了一种熟悉亲切的关系,甚至连一些很私人很琐碎的问题都会拿出来和老师说,她甚至还会向我询问韩剧到底好看不好看……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如我老妈那样亲切慈祥而又有点唠叨的老太太啊,为什么自己当年会这么怕她呢?真是没道理。
最后,想起了一个不知道我是否该称为“老师”的人。因为我是被他扫地出门的弟子。
在我小时候,社会上还没有如今所谓的“素质教育”的概念,孩子除了学习之外没有别的负担。不过我的父母却是走在时代前端的人,从十岁开始,便让我学习琴棋书画之类的“旁门左道”。小学开始,我学的是小提琴(因为小提琴便宜,钢琴好贵),在八年的学琴生涯里,从少年宫到家教,我换过好几个乐器老师,但其中水准最高的却是年纪最轻的那个老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社会尚未如现在这样的开放发达。对于家乡小城来说,出了一个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实属罕见。但更罕见的是,不知为何,那位师从陈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创作者)的人,却居然被分配去了一个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单位,做一份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作。
经人引荐,读中学的我和好友从少年宫里跳槽,成了他的学生。记忆里他是一个很清瘦的人,才华横溢,不仅拉得一手好琴,书法也是一流。第一次见面时,他怀着很饱满的热情和信心看着我们,对家长说他会把我们起码培养成能考上音乐师专的水准。老妈连声说这当然好当然好。不过我心里却知道那不是她的真心话,家里从未指望我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成为一个音乐家,我还是要认真读书上大学的。学琴对我来说不过是培养综合素质和锻炼右脑的途径而已,不过是一个业余的消遣。
果然,这个老师很严厉,第一次上课就不由分说地剪掉了我精心养护的长指甲,令我难过万分。他会用竹枝敲我的手指,提醒我音准不对。几个月后,因为我的琴艺丝毫不见长进,更是屡屡受到不客气的责骂,最后,我只能无奈地对他说了实话:学校里课业太重,回家要做很多作业,每天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练习小提琴,所以学到开塞后就一直停滞不前,那一段《迷娘》始终无法娴熟。听完我的辩解,老师非常失望,看着我,长久地沉默不语,让我不自禁地感到害怕。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们家长,说:“既然无法投入学习,那不必再来浪费时间了。”
他不要我们了。这个消息让少时的我饱受打击。父母更是觉得脸面无光,几次托人劝和,但孤高清傲的老师再不肯收回自己的话。在那个时代,一堂课二十元是不菲的收入,但是他却宁可不再教授两个不能专心的学生,也不愿浪费他的时间。
不知为何,虽然自小听惯了称赞,但在这件事上我只觉得羞愧和难过,却并不恨他的决绝和高傲,甚至在父母对人抱怨他时也会插嘴辩解“不是老师不好而是我自己不够好”,然而,未必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持有同样的看法。这位老师的恃才傲物为他在家长那里招惹了很多嫉恨,而他又是如此清高自诩的人。他得罪了上上下下诸多人,周围很多人视其为疯子和异端,冷嘲热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到后来,他竟然真的因为精神过于压抑而不得不接受治疗,从此病退在家。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已经在大学校园里,只觉得刺心。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在年纪小的时候,我还不懂得,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曾经目睹了怎样的一个悲剧。就在我的身边,那些社会偏见和孤立,是怎样摧毁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当然,令人庆幸的是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在不断进步,十几年后,当我自己也以一个“异端”的形象出现在单位里时,这个社会的包容度已经增加了很多。虽然也是身处一个事业单位,但头儿和同事都很开通和友善,让我从未觉得被孤立和不自在,反而有时候会自愧自己在专业上的懒散和不求上进。
很多年后,我的手指已经失去了灵活,小提琴尘封在匣子里,弦断曲绝,却始终还记得那些练琴的夏日里滴在水泥地面上的汗水,记得手腕的酸疼和手指的刺痛,记得头顶风扇的摇响——当然,也记得老师演奏的那首《梁祝》。那样华美的音色,饱满的激情,缠绵悱恻的《楼台会》,狂风呼啸一样的《哭灵》,和最终的《化蝶》——那些青葱少年时听过的旋律,仿佛还在脑海里飘摇,无论日后我听过多少个其他版本,始终也无法把最初的印象从脑海里抹去。
然而,有些逝去的,已经是再也回不来。
时代和世道果然是在不停变迁,不知为何,听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说起来,如今有些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竟然会紧张对立到如此,完全和我少年时代不同——在我求学的十多年里,被罚过站、抄过书,当然也有过不满和反抗,但是却从未记恨过任何一个老师。我一直对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心怀感激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