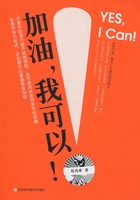他突轻笑了一声,淡道:“退下罢。”
日后却是风平浪静,南宫珏被授予爵位,赏黄金千两,手下将士也是赏罚分明,似是那日看到的“功高欺主”四个大字不过梦幻一场,但朝中大都已明白,这四个字是何等重的分量,亦是历代帝王最难以容人之事,古有杯酒释兵权,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南宫珏此时应赶在之前交回兵权,最起码主动分散手中的权利,可南宫珏每日在府内吟诗作画,对兵权二字只字不提,而皇帝对此事亦是含笑带过,对南宫珏依旧如往日,关系之微妙让朝中人不免暗暗猜测,这君臣二人存的到底是何心思。
领着几个内侍去丝库里取今年的贡品来,道路极长,免不了烦闷,小弥是出了名的好性子,便由着他们一路上说三道四。
“近日来,圣上多有疏远妩妃娘娘,倒是那新封的婕妤频频侍寝,也多有赏赐。”
“咱们这次要取的绸缎说不定大多便是赏给那位婕妤的。听说因是宫女出身,对人很是和善,被调动到婕妤身边的可极是羡慕,可不像那位。”
期间有人想起那婕妤与小弥有点关联,忙住了嘴,偷瞧了瞧她面上,她似是未听见,拢袖目不斜视的走着,这才笑道:“什么话,难道咱们御前的比不上一个小小婕妤的内侍?”众人心中一惊,心道这位典使向来受宠,方才的话可是犯了忌讳,忙附和道:“是极是极。”
远远的行来一行人,为首的银白色暗云纹锦袍拽地,步伐间如行云流水,甚是飘逸俊美,因宫廷中白色甚是忌讳,穿白者甚少,允可着银白衣面圣者,唯有一人,小弥心里突地一跳,低头领众内侍行礼:“见过将军。”
南宫珏习惯的淡淡颔首,目光在她微垂的面上扫过,并未在意。走过几步越觉那眉眼眼熟,细细的回想一番,心里蓦然一恸,可不就是她。突转身喝道:“等等。”
诸人不知何事,驻足等候,唯小弥垂目,他大步走过来在她跟前停下,她头上戴着金丝高官,黑发束起,遮掩在里面,五官便清晰的露出来,数月不见,只觉少了先前的青涩,愈加妩媚起来,似是美玉雕琢过后,愈发的光彩夺目,身量似也高了,已长到他胸前。他沉吟许久,方才哑了嗓子道:“这位典使,先前却是没有见过。”
她心里千思万绪,与他在一起的诸多场景脑中闪过,他待她的好,那分明的温暖甜蜜,却又忆起那份绝望痛恨来,雨中她悸动大哭,丝丝痛楚夹杂,一时竟不知是何滋味,声音竟是出乎意料的平静:“回将军,奴才上任时,将军尚在塞外,因此未见过奴才。”
他见她言语疏离,不由皱眉,情不自禁覆上她的手压低了声音道:“我找你许久。”看她良久,又道:“当时,是我错怪了你……”
他虽压低了声音,内侍们离得却是极近,不过两步的距离,她鼻子蓦然一酸,只怕再听下去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若是左右听到,传到皇帝耳里……惊得频频转头,更不敢看他眼睛,目光闪烁着呵呵干笑:“将军……这是什么话……”见内侍诧异的瞧着她,愈加心虚,手忙脚乱的将手抽回来。
他不由捏的紧了,手上不觉力道已大,竟是痛极,小弥垂下眼,轻声道:“奴才先前不懂事,将军大人大量,便忘了吧,自此以后,奴才与将军依旧是主仆情分。”
袁副官也认出小弥,见她内侍装束示人,南宫珏目光沉沉的瞧着她,那神情分明的复杂难言,顿时捏了一把汗,提醒道:“将军,圣上还在等着将军。”
他才回过神来,看她一眼,幽幽叹道:“走罢。”
内侍挑了帘子,南宫珏偏头进了殿,便见冷烈尚在持卷揽阅,施下礼去:“叩见圣上。”冷烈方才抬起头来,淡笑道:“卿来了。”吩咐左右:“赐坐。”南宫珏忙道:“谢圣上。”宫女上了茶来,殿内焚着沉香,幽幽似缕,南宫珏沉吟许久,方才道:“圣上,三座城池守护之事,臣觉不妥。”
冷烈唇边含笑,只是挑眉:“哦?”
南宫珏道:“柴将军和臣的两位下属素来不和,若有战事,只怕难以协作。”
冷烈眸中一禀,淡道:“卿的意思,可是怕柴卿假公济私?”
南宫珏忙站起身来:“臣不敢。”冷烈微笑道:“柴卿性子耿直,是名难得的战将,只是难以与人相处,卿好生提点才是。”他放缓了声音,颇为为难道:“况朝中对刘、鲁二位将军的派属亦有异议。”说完只是淡淡看着他。
南宫珏面色平淡,垂目不语。
一时似是空气凝固,天边有乌云压下来,暗沉沉的凝在心头,似是刀剑相击,锵锵作响,涌动无声的较量。
良久,南宫珏眼睑一动,低头道:“谨遵圣命。”
冷烈敛了神色,微微一笑:“卿能体谅,朕心甚慰。”
内侍在门外通禀:“圣上,禄王爷求见。”
南宫珏闻言躬身一礼:“臣告退。”
冷烈点头,南宫珏退下,禄王大步就冲进来,“扑通”跪在地上,苦着脸道:“四哥,臣弟失察!”
他在他面前鲜少行大礼,不由一怔,笑问:“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