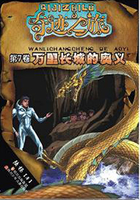大灰停住了脚步,嗯哪、嗯哪地放声大叫,还把两个前蹄抬起来,人一般地站着。
天什么时候黑了?大灰是灰色的,树是灰色的,草是灰色的,远处的山是灰色的,脚下的地面是灰色的,我是灰色的吗?不知道,因为大灰不会告诉我,大灰侧眼望着前方,前方是望不到底的黑,有腥味悄悄涌过来,有风轻手轻脚地抚过我的脸,咸咸的,湿湿的,还有一种异样的动静,我知道,是水推着水。我转过脸望右手边的天,天色深蓝,似茄青,一颗星贴在山顶上空,亮得扎眼,那是金星。金星在西。那么前面是南方,那无边的黑就是大海了!海上方星星一点一点,自在,悠闲,没心没肺。忽然,一颗星不小心跌下来,三蹦两跳,在水里消失了踪影,一条鱼也没惊着。大海在南,大海的南边是哪里呢?是爪哇,爪哇。爪哇国里有皇帝吗?!
胸前一片冰凉,噢,我满脸是水,泪水,咸得发苦的泪水。我放声大笑,把所有的泪水都笑了回去。
大灰有些不解,不住喷着鼻子。我突然想起了“云里雪”——我不吃肉,我天天吃“云里雪”不成吗?!
该回去了。
星星渐渐黯淡下去,天渐渐由青变蓝,快到木兰溪边的时候,月芽已爬上了木兰桥边的柳树头顶,月芽太沉,把柳树的脖子都压歪了。
咦,是谁可着嗓子在喊什么?仔细一听:反清复明!反清复明!
停了一会,喊声又起,颤颤巍巍:清贼残暴,火烧少林!
柳树背后,隐隐约约的一个长人,和柳树差不多高,白衣白帽,纸影子似的,颤颤巍巍,晃。
我双腿一夹大灰,大灰啪啦啦冲了过去。
白衣长人晃了又晃,终于没能躲过大灰的脑袋,翻倒在地,折了,一人折作两人。
下面那人黑衣黑裤,如果不是有脸,你根本就看不到他。上面那人看不到脸,不知是不是抹了炉灰,因为白裳太长,他作势要像鲤鱼一般跃起时绊了一脚,结果又在地上滚了几滚。
我说,海东边过来的吧?
两人的眼一绿,手往腰后摸去。
我说,着什么急,你们看,我像那种人吗?
黑衣黑裤吁了口长气:是,我们是延平王派来的,扮冤魂,叫人们起来把清狗赶出去。
我说,你们刚才喊错话了,嵩山少林还在,这两天,有两个那里来的和尚在栖霞寺弘扬佛法呢,信男信女比苍蝇还多,没人会信你们的,再说,赶走了清狗,却待如何?
我的话还没掉到地上,白长裳就抢上来:汉人当皇帝!延平王当皇帝!
我说,没有皇帝难道不成吗?
他们沉默了一下,齐了声:你这个神经病!没有皇帝怎么成?!不跟你说了。
他们重新叠起,一晃一晃地走远了,他们的身形太长,远远望去,实在吓人,活脱脱一条冤魂。突然,远远的又传来他们的喊声:清贼残暴,火烧南少林!
我愣了一愣,差点晃倒,幸好手里有竹竿,赶紧杵在地上。竿头的胡萝卜正好伸到大灰的嘴边,大灰脸一撇一扯,萝卜不见了,差点把竹竿也扯走。大灰咔咔两声就把萝卜吞进肚子里,大概是对自己动作的敏捷程度颇满意,它忍不住嗯哪嗯哪又叫唤了几声。
气得抽了它一竹竿:你这死奴才!
丈人家的门开着,灯光如水,溢到院子里,仙人掌围成的篱笆墙绿了一半。
是娘子的声音:我家相公到哪里发神经去了?
啊,娘子口音已改,如母亲,一口清河腔!
胸口一阵酥麻的温热,立马化为冰凉,冷汗一粒一粒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