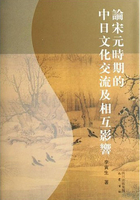北刘村快到了,我知道过了北刘村,很快也就到家了,我可能再不会和老根有这样独处的机会了。其实我没有很复杂的想法,我就是很珍惜当时的时光,那趟旅程。
老根不说话,我虽确信他心里有过我,这种事各人心里都清楚。但我气他不说话,不把我的话当话。又想到他很快就成公家人,找公家闺女,我的心都快碎了。我难受得不知怎么办好。想哭,但又感觉自己很可笑。这样闭了声,又不甘心。
到了北刘村,老根停了车,我也跳下来。他撑住他的“凤凰”,到直冲北刘村的五干渠桥底下小解。我站在当处,看着不远处我们村,绝望,绝望——
就在老根扎腰的时候,我唿唿跑下桥,到他身后二话不说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
老根喘着气,将自己从我怀里手里拽开去——他在我手心里唿地坚挺起来,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软下去,弄得我一手精湿。
我刚爬上桥面,老根已经拽着裤腰,跑出去老远,我骑上车去追他,直追到村口。他站下,我也停下,他蹁上车,我跳上去,回了家。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好多天,我都没见到老根。我为自己做的事后悔。我以一个过来人的不尊重侵犯了老根的纯真,我后悔不迭,我盼着能有机会弥补。
可一直没见到老根,又一天,陈生银过来问我,说是不是老根到镇上见了什么人,知道他调不成了,或者遇了什么事儿。我说没有啊。那天办完事就回了,快得、顺得很。陈生银应着道,噢,噢。那咋回事儿,老根这几天不吃不喝,不走不说,和傻了一样。今日我去镇上,听说调动名额下来了,我准备给他说说去,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去县城上班。
不知陈生银怎么问的,反正老根没去县城,没去当公家人,当然也没找公家闺女。后来我却稀里糊涂地到了县城,成了公家人,和陈生梁团聚了。我啥也没敢问。
但我心里有事儿。见到村里或近处村来的人,我就拐弯摸角地打听老根,有时候人家说,还是那样,没神了。也有时候说,不知道,没怎么听说。
又一次,陈生银来县城办事,在我家住下。我倒没问,他与陈生梁喝着酒说起:
在村里我没敢说,我看哪,八成是中了邪了,萎萎缩缩了几个月。唉,死前对我说,一定把他埋到五干渠桥底下,这哪儿是埋人的地方!
讲完了,我松了口气。
我相信类似的人,类似的事,以前很多,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但是,对于我,只记下老根了。
后来我同一位加拿大汉学家约翰聊天,我将老根的故事讲给了他。当然,我将陈麦穗换成了小芬,将老根换成了大民。一些细节——文中没有的细节被我即兴想起,一并讲于约翰,说起村里炼炉和旧址还在,牛棚旧址上建了乒乓球室,我还说陈生银家还用着那个军用水壶,还说——引得约翰非要去现在的望洋坡,也就是当时的向阳大队看看。刚开始我说不行,远得很。我嘴里这样说时,是怕看到的会削弱故事的份量,这是我的自私,不过我的意思是想让这个故事,让老根在约翰心里鲜活一些,神密一些,余味无穷。我不想他去看看那个地方,感觉被我骗到,最要命的他再想“整个故事,只不过是我的杜撰”,那我就——所以,直到2003年底,我没答应带他去。2004年2月某日,天气很冷,约翰给我电话,说要来我家坐坐。我说欢迎。
我打开门,可约翰并不进来,他说: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了。可是,你是错的。今天,我就是问你一句话,最近,不,明天,你愿不愿意带我去望洋坡看看,炼炉、牛棚、水壶、五干渠桥。约翰用些有生硬的汉语讲完,执意站在门外不进来。我知道他是真明白他说的那些。所以我说,OK。
我连着带他去了三趟,一次我们趷蹴在炼炉遗址上,约翰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一直想不明白,那是种什么样子的状态。我说:不怨你想不明白,也许,你没经历过那些,你知道吗。我拿手比划着:这么说,有这种体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大的,明白吗,很大,很大的环境造成的,如果说野蛮的排斥掉个人的东西原因不对的话,加上它,也同样不那么恰当。约翰耸了耸肩,和我对他一样对我无奈。
约翰朝我凑了凑,比划道:知道吗,如果是我,真是像你说的这样,我就,他朝我做了个拥抱的姿势说:我就要爱她,我不在乎英雄,也不在乎连她妈妈都不喜欢她,说她没人要。我知道他不会真的拥抱我,但还是往后闪了一下。我对约翰说别想太多了,这,只是个故事,而你,和我不一样,你不应该留恋这个故事,你年轻,有朝气。你有你自己还想像不到的爱情和故事。你和大民和小芬不一样。他们,只属于他们的年代和他们自己。
约翰看着远处,喃喃地说:不,他们不只属于他们,他们还属于,你。
我看着远处,没说话。
又过了两三个月,大约是“五一”前后吧,约翰跑来告诉我:他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到望洋坡小学义务助教的“请求信”,正在待批。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慢慢喝完,然后愉快地哼着歌走了。
我想说他做这个决定前,该同我商量一下,或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但是,想到他和我,和我们的不一样,就没开口。
2004年9月26日,我收到约翰的信,说已经在望洋坡住了整一月了,说感觉很棒,还说几乎天天到“炼炉”旧址和那个小桥底下转一圈,“与大民对话”。还说这里的孩子们很可爱。
2004年12月20日,收到他的信,说祝我圣诞快乐,还说让我也祝他快乐。在信的末了,还说了要自费做一个仿制的自由女神像,放在炼炉旧址处。
2005年3月12日,植树节,他在信里说他爱上了村支书的女儿陈康晴。他在信中说:Miss陈,美丽又善良。
2005年5月31日,他信中说,他参加了义务建设校舍的活动,感觉很荣幸,但,为此残疾了。不过,Miss陈说一样爱他。镇上县里市里,甚至省里领导都到医院看望了他。给了他一面大锦旗。他说一切让他很感动。
2005年7月3日,他来信:陈书记不顾他们的抗议,将陈康晴送到外地一个亲戚家了,他说他感觉很绝望。
2005年9月18日,他在信中说他要去找康晴,一定去找她。
2005年12月25日,圣诞节,他的信中没有说祝我圣诞快乐,只说不知道去她亲戚家的路,连孩子们也不肯告诉他。
2006年2月21日,我给他回了封信:回来吧,我们都很想你。
2006年4月25日,他从北京直飞温哥华。
前些天,收到他的邮件,他说,他现在一家野生动物园,任植被恢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