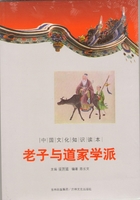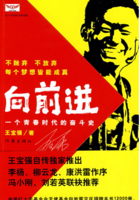在20世纪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中,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成就比较突出的两位,他们分别在《新理学》和《论道》中建构了一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由于两人共同的思想背景(均接受了20世纪初流行于英美的新实在论),以及大致相同的思维路向(均服膺逻辑分析法,并用它来重新解释、组织和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这两个系统通常被看作是十分近似甚至相同的。例如,贺麟在四十年代就认为:“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先生的《论道》,在基本概念上是相同的。冯先生所谓理,相当于金先生所谓式,冯先生所谓气,相当于金先生所谓能。由无极之气到太极之理,所谓‘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形成‘流行’的实际事物的世界,两人的说法也是相同的。”再加上写作过程中冯、金二人过从甚密,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更显得确凿无疑。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冯、金二人各自系统的独立性将大为减弱,这关系到他们哲学地位的评价问题。为了澄清事实,本文希望能够从内容本身出发,对这两个系统进行粗浅的比较。下面将首先分析一下《新理学》的形上系统及其内在难题,然后把它和《论道》进行比较,希望借此能够证明:第一,这种近似或相同只是十分表面的现象,由于所赋予的意义不同,这两个系统从概念的选择到体系的建构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第二,《论道》对问题的解决远较《新理学》深刻,其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晦涩和艰深。
一、《新理学》的形上系统及其难题
《新理学》是冯友兰“贞元六书”中最初的一本。作为整个系统的纲要,这本书涉及心性、道德、历史、学问、艺术和修养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在自然观方面,它集中地讨论了存在的终极本原问题,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宇宙发生模式,其中对共殊关系的处理决定着新理学系统的逻辑发展。
就自然观而言,《新理学》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通过理智的分析,把事物追溯到它最简单的构成成分,即所依照者理和所依据者气;然后又通过理智的总括,得到两个总体观念,即总一切流行的道体和总一切有的大全。理、气、道体和大全是新理学的四个最基本的观念,冯友兰认为:“真正的形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提出这几个观念,并说明这几个观念。”
在冯友兰看来,形而上学和其他知识一样,也从感觉经验出发:“哲学始于分析、解释经验,换言之,即分析解释经验中之实际底事物。”但哲学的分析解释却与普通科学有本质的差别,科学的分析是实质的、有内容的,它提供关于事物的实际知识,而哲学的分析则是形式的、逻辑的,它提供的只是事物形式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于实际无所肯定或很少肯定,但它对一切事实又无不适用。正因为形而上学有这种特点,所以它和经验之间就只有单向的关联,我们获得形而上学知识要靠经验,从经验出发,但这种知识一旦获得,它就再也无关乎经验了,实际上,经验对于形而上学来说只起一种阶梯作用,一旦越过,阶梯就失去了效用。因此,冯友兰认为,形而上学的功用,本不在于增加人们对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它的命题和观念也就仅在于形式和逻辑方面,其方法仅限于理智的分析和总结,因此它的结论就不受现代科学的发展给形而上学招致的许多批评的影响,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
冯友兰认为,通过这种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件实际的事物都由两方面要素构成:所照者理和所依据者气。所谓理,是指一事物之所以为事物者,如方之所以方,圆之所以圆,理是具体的个别事物所依照的标准和原型,有似于柏拉图的“理念”。所谓气,是指构成事物的终极材料,是任一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气没有任何性质,不可言说,不可名状,因而不同于原子、电子等实际物,只是一可能的存在,一逻辑的观念。有理,有气,我们通过“形式的总括”,就可以得到形上学的另外两个主要观念:道体和大全。总所有的理,构成理世界,也叫太极;而真元之气因为无名无性,故为无极。由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就是我们实际的世界。因为任何一件实际的事物都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所以实际的存在就是从无极到太极的流行。总一切的流行就叫道体:“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无极、太极、无极而太极,总括起来,统而言之,就叫大全,也叫宇宙:“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冯友兰认为,像道体和大全这样用“凡”或“一切”表示的词,才真正是哲学的概念,因为它表明这种普遍性的知识是超越经验的。道体和大全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对于它们,我们只能够用负的方法给以表显,但这种表显毕竟也是讲形而上学的一种方法。这样,冯友兰从经验讲起,通过形式的分析和总括,得到了理、气、道体和大全四个超越的观念。由于其中三个所拟代表的,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形而上学被推到了它的逻辑终点,即在最终结果上,形而上学是不能讲的,于是冯友兰总结道:“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
《新理学》的形上系统大致如此。它借助于形式化方法,从经验中的一点向两极纵深处扩展,一方面分析剥落,追溯事物构成的终极要求,一方面归类概括,获得关于宇宙大全的整体观念,而许多细节方面的推演均被安排在这双向的程序中,由此描绘出一幅宇宙构成图景。在这幅由概念交织成的画面中,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范畴如理、气、无极、太极、道体等都被赋予严格的涵义和精确的定位,许多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或者得到了重新的解释,如“理一分”、“无极而太极”等,或者被作为无意义的问题而取消,如“理气先后”等,这显示出逻辑分析的巨大威胁,使新理学在形式方面远远优于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所有中国传统哲学。
但是,形而上学问题决不像新理学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几个超越的观念不可能把长期争执的问题一下子解决,相反,我们看到,新理学正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说气作为构成质料和事物的关系还可以理解,那么事物所依照的理和事物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呢?既然理气等概念都是静态分析的结果,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人们如此熟悉的变化呢?特别是,如果形而上学最终结果竟是“必须静默”,那么人们如此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学,与人类理智所进行的无聊把戏,又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理事关系问题,冯友兰用共殊关系来解答。冯友兰认为,理就是共相,事就是殊相,理事关系实际上就是共殊问题,一般和个别关系问题。冯友兰接受了英美新实在论的观点,坚持一种彻底的客观论:“我们的纯客观论则主张不独一件一件底实际事物是客观的,即言语中的普遍名词或形容词所代表者,亦是客观底,可离一件一件的实际事物而独有。”言语中的普遍名词或形容词所代表者,即理或共相,这些理或共相是个别事物所必须依照的,但它们之有并不需要个别事物的存在作保证,因而可以离开个别事物而独有:“所有底理,如其有之,俱是本来即有,而且本来是如此底,实际中有依照某理之事物之存在否,对于某理之有,并无关系。”因此冯友兰反对就存在意义上说“理在事中”或“理在事上”,永恒的理本身根本无所谓存在不存在问题。
冯友兰由于取消了理的存在问题,在先后问题上,他也就排除了理事在时间上谁先谁后的考虑,因为理是超时空的,“它之有是不能用关于时间之观念说底”。但他认为,理事先后还是可以说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逻辑先后关系。所谓逻辑先后,是指一个命题和它的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它通常用逻辑上蕴涵关系来表达。按照冯友兰的看法,从有事物可以推得有某理,但有某理并不需要个别事物的存在作保证,因此有理就一定在逻辑上先于有事物,推而广之,“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底世界”。这样,冯友兰借助于形式化方法,把理终于提升到具体事物之上,把理世界和现象界彻底分离开来,从而获得了一个冲漠无朕、万象森然的洁净空阔的共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