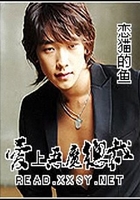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它们调和相处,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带蜜黄,不太宽,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确是“走了样”的“和玺椀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在那几年里,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从这段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地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么独到的功夫(这本大型专业参考工具书后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古往今来,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五三年三月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术方面的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做一两种重要建议。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某某等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敏思遐想,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组停轧钢筋;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第三,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除了组织工作,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为了不使我的这些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复对照、研究,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吴良镛、刘小石:《梁思成文集?序》)。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
从五四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对比中外,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大约在五五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着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每当学生来访,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而决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顾问”作风。这里,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华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她。“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被他们砸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作为她的后代,我们想,也许就让它作为一座无名者的墓留在那里更好?
母亲的一生中,有过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但总的说来,艰辛却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与能力似不相称。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不论是建筑界、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包括一些外国朋友,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一九五三年前后,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她审稿并作“序”,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批评,其最后几段如下:
……
两层梁架上就只点出三块红色的主题,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全梁青、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乱。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四)青绿的变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学生走后,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
谈起外国朋友,那么还应当提到,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一九七九年来访时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父亲所写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她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而且已经开了头,但后来大概是一个未能完成的项目。
总之,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顶”时,曾经挖苦地说:“梁思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常气力不支,又古又洋,所谓修养,既能争论魏风唐味,又会鉴赏抽象立体……”这些话,当然也适用于“批判”母亲,如果不嫌其太“轻”了一点的话。二十世纪前期,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汇中,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人物的出现,谑语雄谈,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又太少了吗?对他们的“批判”,本身就表示着文化的倒退。那结果,只能换来几代人的闭塞与无知。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子,同清宫中太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时间,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强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许多人曾对我说过:你母亲幸亏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两年,“反右”那一关她肯定躲不过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对于她这样一个历来处世真诚不欺,执著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体验一下父亲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所经历过的一切,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我简直不敢想象。“文革”期间,父亲是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顶着全国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
一九五五年,就在床褥之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够通过这本文集,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