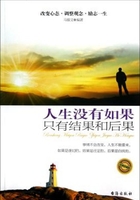李穆然与冬儿听庾渊讲完了云台二十八将之事,云台楼的饭菜也已陆续上了桌。
庾渊给三人都满上了酒,道:“说了这么多,在下还没有自我介绍。在下姓庾名渊,是生意人。不知二位朋友怎么称呼?”
李穆然看他一直用鲜卑语讲话,心知他是看自己二人穿的鲜卑服饰,便以为是鲜卑人。他索性将错就错,想了两个鲜卑名字,哑着嗓子回道:“我叫做鲜于牧,这位是我的兄弟,鲜于冬。跟庾兄弟一样,我们也都是生意人。”
“哦?”庾渊神情甚是诡异地笑了笑,举起酒杯来,道:“说来我们也只刚见第二面,但总觉得和两位甚是有缘,便干了此杯吧。”
李穆然、冬儿与他一碰杯,各自仰头灌下,只觉那酒味清冽,辛辣之余,更有丝丝甜味。李穆然是喝惯了酒的,自然无碍,但冬儿喝下一杯后,便被呛得咳了起来。李穆然忙轻拍他背心,又对庾渊笑道:“我这小兄弟才从家中跟着出来。还没喝惯酒,让庾兄弟笑话了。”
庾渊道:“这酒是用龙山泉水酿就的,味道和你们的马奶酒不大一样。鲜于兄弟喝不惯,那也很正常。不知两位一路南下,是要到何处去?”
李穆然心知庾渊多半是要去建康,自己前往巢湖,方向几乎一致,暗忖万万不能告诉他真实目的,但若说的全不一样,万一这之后在路上再碰到,当面被揭穿,也难免有些说不过去,便道:“我们贩了些皮毛到池州,顺便再从安庆进些灵芝回来。”
“安庆啊”庾渊微微皱起了长眉,似乎在揣度着什么,他心不在焉地夹着菜吃了几口,忽地仿佛打定了主意一般,轻轻一拍桌案,道:“既如此,到六安前我与两位都是同路,不如我们结伴而行,如何?”
李穆然淡淡地瞟了他一眼,又灌下杯酒去,才不慌不忙地说道:“庾兄弟,我们俩兄弟习惯两人结伴而行,你跟着我们一起走,恐怕不大方便。”
庾渊笑道:“这个简单。大家都是生意人,鲜于兄不妨开个价。在下只是想着最近北面不大太平,咱们一起走,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他如此开门见山,李穆然心中暗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恕我直言,庾兄弟是不是惹了什么麻烦?”
庾渊脸色一僵,不过心知这两人早已见识过了蛇公子的手段,自己也没什么好遮掩的,遂笑道:“鲜于兄,你们两位武功远胜于在下,既然同道,就顺便搭伴,在下也绝不会碍二位的事。更何况,在下手头也算宽裕,我们生意人凡事讲的便是一个‘利’字,这般帮人又利己的好事,二位何乐而不为呢?”他说得很诚恳,虽然是在请求对方,但语气始终不卑不亢,倒叫李穆然刮目相看。
瞧他一脸悠然,若不是自己知道蛇公子是何等可怕的人物,断然猜不到他此刻内心的不安与惶恐。李穆然微微一笑,忖道此人果然不简单。光看这份城府,这份谈吐,便不在慕容冲之下。他不想多生枝节,毕竟一起行走,结伴时间越久,易容之事就越容易被看穿。他想着该如何拒绝,正暗自思量,却觉脚下一动,是冬儿轻轻踢来。
“穆然,这人说得也对,你打算怎么办?”她面上也在吃着菜,实则用出了“传音入密”的功夫,腹语暗言,似是动了恻隐之心。
“你想帮他?”李穆然密语问道。
冬儿看了他一眼,眼中露出些期盼,随即又传声道:“他用的功夫是谷中的,应该和我们有关系。我瞧他不像是坏人,你难道要看他遇险么?他既然是晋国人,路上我们也好先跟他打听打听消息。”
“罢了。”李穆然暗叹一声,心想一路送到六安,短则月余,长则四十天,勉强也混得过去。更何况庾渊是玉宇阁的东家,酒楼向来是消息流通之处,他知道的轶闻杂言,应该比平常一位士族公子多许多,冬儿所言,也不无道理。想罢,他深吸口气,又饮了一口酒,却仍想套对方的底线,便在桌下对冬儿摆了摆手,并不说话。
庾渊看他两人都不发话,心里有些发虚,但面上仍是稳如泰山。他见李穆然的酒杯空了,又随手满上,笑道:“鲜于兄,此间酒菜可否合胃口?”
李穆然“嗯”了一声,既然对方不提,那他也乐得拖下去,反正被蛇公子追杀的人又不是自己,怕什么呢。
倒是冬儿见那两人谁也不提方才的话茬,颇有些坐立不安,然而李穆然既不发话,她也就不能出声,只觉憋得难受,不知如何是好。她喝不惯酒,也觉饭菜口味一般,吃了几筷,便放下了筷子,怔怔地盯着窗外的白河出神。
庾渊见了,心知这位“鲜于冬”城府远比那位“鲜于牧”要浅,遂笑道:“鲜于兄弟,可是觉得此间饭菜不合胃口么?”
冬儿听他问自己,忙粗着嗓子回道:“不是。做得很好,只是我吃不惯罢了。”
庾渊笑道:“这道‘云台冻鱼’是这儿的招牌菜。这时天寒地冻的,鱼肉反而肥美香滑,想来鲜于兄弟此前长居草原,你们吃的都是牛羊肉,吃不惯鱼,怕被刺到。”他用筷子从鱼腹处夹下一大块肉来,极轻巧地除去其中几根长刺,夹到冬儿面前碟中,道:“这一块是没有刺的,味道也是最好,兄弟不妨试试。”
他如此殷勤款待,冬儿又实在没有李穆然那般的厚脸皮功夫,不觉满面发烫,转脸看向李穆然,低声道:“大哥,你”
李穆然无可奈何,淡笑一声,道:“庾兄弟,实不相瞒,你的对头很厉害,我和我兄弟都是普普通通的生意人,学了些功夫不过是为了应付道上的强人。恐怕帮不了你太多。”
庾渊微笑道:“鲜于兄过谦了。追杀在下的那位,这时已经追到了前边去,我们走得小心些,倒也不是一定就会撞上。更何况集咱们三人之力,对付他一个人,应该不成问题。”
李穆然冷笑一声:“若我猜得不错,庾兄弟那位敌人,应该不止一个人。他手下千千万万就算是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遇上,也是胜不了的。”
庾渊明白他说的是蛇公子统御的毒物,“呵呵”笑道:“是在下疏忽了。”随后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道:“这瓶子里装的是驱毒药丸,只要口中含着一颗,保管那些毒虫不敢近身。”他极大方地把一整瓶都递给了李穆然,又道:“鲜于兄留在身上吧,我这边还有。”
李穆然不动声色地将那瓶药递给了冬儿,冬儿打开瓶盖,轻嗅了嗅,闻到的起初是雄黄、艾草的气味,可是之后传出的馥郁幽香之中,有好几样她也闻不出来是什么。她微微一惊:这药的配方在谷中没有,不知是不是这位庾公子自己配的。
庾渊看她辨药,加言道:“鲜于兄请放心,这是蛇公子自己带在身上的解药,断断错不了。”
“蛇公子自己带在身上的?”李穆然大吃一惊,瞪向庾渊,“你和他究竟结了什么仇?”
庾渊笑笑:“鲜卑四公子的名头果然响亮,连鲜于兄这般的普通生意人也知道他的名号。”他这句话似乎是在讽刺李穆然的身份,李穆然却没心情计较,只是连声催问。
庾渊又是一笑,神情甚是得意:“也没什么,不过是为了女人争风而已。这药也是他身边姬妾拿来送我的。”
李穆然闻言初始一愣,旋而则不禁“哈哈”笑赞:“庾兄弟真是好大的胆子。”
庾渊莞尔:“所谓色胆包天,人皆有之。”言罢,一举杯,与李穆然碰杯而饮。
此后两人借着酒劲越聊越热乎,那庾渊以为桌上的都是男子,说话间不必避讳什么,口中荤段子不断,直讲得冬儿面红耳赤,几次想起身离席。
她暗自传音叫李穆然早些想办法脱身离开,却见李穆然和那姓庾的相谈甚欢,竟似转眼间成了无话不说的知交一般。冬儿心中强压着恼火,直到见饭局将了,庾渊竟盛情邀请二人去百花楼过夜,不由得再也按捺不住怒意,冲李穆然狠狠瞪了一眼,便甩手而去。
庾渊喝得有些酩酊,不知自己哪句话得罪了对方那位小兄弟,正要追上去问个究竟,就见李穆然在面前一拦,道:“庾兄弟,我们已经定了客栈,百花楼恐怕去不了了。明日辰时三刻,我们约在百花楼下见面,一起离开南阳,如何?”
庾渊笑着点了点头,然而一句“告辞”还没讲出口,就见那男子已匆匆离去,不消片刻,便到了云台楼之外,追上了前面那矮个男子。
“身法行云流水,这人武功应该不在蛇公子之下。另外那人武功虽然弱些,但也算是一名高手。”看着那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庾渊之前的醉意一消而散,眼神也尖锐了起来。
“兄弟,你慢点走!”李穆然紧赶慢赶跑到楼下,见冬儿自顾自往前走,始终不回头,心中着急,不由在后边哑着嗓子喊了起来。
他的轻功高于冬儿,可是在人群之中总不好施展,便只有不住地说着“劳驾”、“让让”,在人群之中生生挤出了一条路,好不容易跑到冬儿身后,伸手一把拉住她胳膊,笑道:“你真生气啦?”
冬儿的身子还在不住地抖着,她强忍着泪,一甩胳膊,道:“你拉我干什么,跟他一起去百花楼就是了!反正你们志同道合的,我在旁边也是多余!”
李穆然忙道:“小声些,小声些!”拉着她又走远些,见身边人不多了,方压低了声音道:“傻子,你以为他说的都是实话么?”
冬儿一愣,木木地看着他,细想了想方才二人说笑,道:“不是么?不然那蛇公子为什么追杀他,他又从哪得来蛇公子的解药?”
李穆然笑道:“就算是,也是半真半假。他是晋国人,再怎么好色,也犯不着冒死到秦国的地盘上蛇公子的姬妾。你别忘了,蛇公子是姚苌的手下。”
冬儿虽不像李穆然那般习惯性地把人都往坏处想,可是也转念甚快,被李穆然这一提醒,立刻明白了过来:“你是说,他是借机从那些人身上套消息?”
李穆然喟叹道:“我是说,他和我是一样的人,多半是晋国派来的细作。”
“他和你是一样的?”冬儿微微一怔,又摇了摇头,“那他还这么招摇,去百花楼包人家的头牌?更何况,他是晋国人,连你都知道他的身份,他怎么做细作?姚苌他们不会防着他么?”
李穆然道:“他是比我光明正大得多,也因为是这样,反而更不容易叫人起疑心。你看,他的性子就是招花惹草的,惹出一两件风流韵事来,说不定还被传出一段佳话。可是闺阁私语,他又是个聪明人,哪怕只通过对方的只言片语,甚至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也能套出些消息来。我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但看蛇公子的反应,想来那消息应甚是紧要,否则他也不会亲自千里迢迢来追杀这姓庾的。你想,他的身份两国皆知,真要死在了秦国境内,反而会惹出风波。蛇公子断不会只因为姬妾出轨,就如此马虎行事。”
“是么?”冬儿默然垂下了头,看来自己还是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了。她想通之后,对李穆然原本的怒意也全化为乌有,反倒诚诚恳恳地认起错来:“都怪我方才鲁莽,搅了你们的局,要是他起了疑心”
李穆然打趣笑道:“没什么,我明天就和他讲,你是头一次跟着大哥出来做生意,小孩家没见过世面,去百花楼这种风月场所害羞也是正常。”
冬儿脸上一烫,哼了一声,道:“你你还笑我,那你是常去的了?”
李穆然忙笑道:“冤枉,我我真是从没去过。”言罢,他抬头看了看天,道:“时候不早了,再过一个时辰恐怕要闭市,咱们还是赶紧去买干粮吧。明天启程,这之后到信阳还有一大段山路要走,咱们要做好准备才行。”
冬儿倒也不信他会去青楼,不过瞧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还是起了几分好奇,看他走在前边,自己则踱步随在后边,低声问道:“大哥,你说他和你是一样的人那你以后会不会为了得到消息,也去也去”
她没有全讲出来,但李穆然也明白她问的是什么。他低声回了一句“不会”,可是心中却隐隐觉着,自己恐怕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