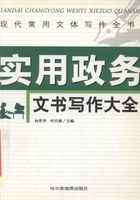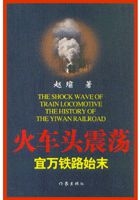他冷笑:“我不屑!我只是想看看你接到喜帖的反应,结果你魂不守舍地开了车走了;我回家等你到晚上十二点,你才像个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回来,我忍了;今天你又想打探他的消息,我偏不告诉你,你又掉了魂似的回家赌气。别人眼里大概还以为我怎么得罪了你,孰不知你满脑子别的男人。”
她万万想不到他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生生挨了一闷棍一样,好半晌才说:“当初结婚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不爱你,你也没有要求过我要爱你。”
他说:“不用拿这样的话来堵我。”俯身抓住她的衣襟,“我只是希望大家面子上都下得来。”他的目光直直地望进她眼中,看清她的恐惧,“官洛美!好好地敷衍我,不要连敷衍我都不屑,否则你一定会后悔!至于你的爱人,我知道你维护他,大概维护得连血海深仇都忘了,可惜我不会忘记我的仇恨。我绝对会把他碎尸万段,然后装在礼盒里送到你面前来!”
洛美失色尖叫,他已用力摔开她,摔门而去!
容海正这一去,就是几天不见,洛美病了几天,四姐要请大夫,她也不让。最后到底还是自己慢慢好了起来,只不过每天早上起来还是头晕,饭量也减了。
容海正终于打了电话来了,他人已在美国了,听到说洛美病了,就叫四姐让洛美接电话。
洛美无精打采的,“喂”了一声,容海正听她恹恹的,想必是真的病得很严重,口气不由得缓了下来:“我下个礼拜就回来。”
洛美“嗯”了一声。容海正问:“有没有发烧?”
“没有。”
“那就好,去看看医生吧,不要自己乱吃药。”
“我没事。”
“那好,你多休息。”
洛美连“再见”也没有说,就将电话还给四姐了。四姐问:“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洛美不想说,就问:“我想吃碗甜食,厨房里有什么?”
四姐忙说:“有豆批、芋泥,还有青梅羹。”
洛美说:“那就青梅羹吧。”
四姐倒怔了一下,微笑说:“太太,厨房里还有酸凉果,那个酸酸的更好吃,要不要一碟?”
洛美点一点头,四姐一阵风似的喜滋滋地去了,片刻工夫就端了羹与果子来了,洛美因为口中无味所以不太爱吃饭,现在两样东西都是酸的,倒很对胃口,不知不觉间就吃完了,几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一吃起兴来了,又叫四姐再去添了一碟来。四姐乐得眼都眯起来了,洛美莫名其妙,又不好开口问。
过了几天,容海正果然回来了,洛美站在露台上看到他的车子驶进来,过了片刻他才上楼来,洛美本以为那日摔门而去后,他必然又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样子,谁知他上来,竟然待她十分温和:“怎么又在风头上站着?”揽着她的腰进房间,告诉她说,“迪奥的发布会上我已经替你订了两套衣服,想不想去巴黎试穿?不想的话叫他们飞过来好了。”
她不置可否,这倒使他误会了,伸手试试她额上的温度,不解地问:“哪儿不舒服?”
她摇了摇头:“我想睡一会儿。”
“那就睡吧。”他替她盖上被子,低声说,“你睡,我下去一趟,还有公事要交代孙柏昭。”语气几乎是温柔的了,说完还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洛美心里疑惑,他上一次这样吻她是在什么时候?
他走了,洛美却睡不着了,口又渴得厉害,于是穿了睡衣起床下楼,想去厨房喝杯果汁。孰料刚刚从楼梯走到拐角的地方,就听到四姐那带着浓重闽南音的普通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啦,不爱动,又不大吃东西。”
容海正说:“总得叫她去看看大夫。”
她一路走下去,楼梯上铺着很厚的地毯,她又穿了一双软底的拖鞋,走起路来无声无息的,容海正冷不防抬头看见她正走下来,立刻煞住了话,叫了声“洛美”,迟疑了一下,才说:“你下来做什么?这里比卧室要冷多了,怎么不多穿件衣服?”
她说:“我要喝杯西柚汁。”
四姐立刻说:“我去榨。”
容海正说:“榨了送去房间。”对洛美说,“我们上去。”
洛美已隐隐猜到了一两分,进了房后,装作无心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将床头的小屉打开了翻检。容海正问:“你不是要睡觉么?又找什么。”
洛美说:“我睡不着,头又疼,找上次那种定神糖浆。”
容海正说:“不要吃西药,糖浆可以吃一点儿。”
洛美趁他去露台上吸烟,将药屉里的一个小匣打开,里面有个白色的药瓶,她拿出来,里面还有没吃完的大半瓶药,倒了一颗在掌心细看,终于觉得异样,翻过来一看,小小的药片上面竟然印着:“VC”。她心里又气又苦,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狼狈与尴尬,不由一顿足,叫:“容海正!”
他极快就走了过来,口中还在问:“怎么又连名带姓地叫我?我又怎么得罪你了?”
洛美不答话,只将手中的药瓶往床上一扔,脸上已是红一阵、白一阵,半晌才说出话来:“你算计我!”
容海正先是一怔,而后反而笑了,说:“我怎么算计你了?这能叫算计吗?”
洛美听他这样说,明显是耍赖了,她心里着急,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了,口中说:“你这样骗我。”
容海正见她哭,也不着急,笑着拍着她的背:“我怎么骗你啦?你哭什么呢?有个孩子很好啊,说不定长得会像你呢。”
洛美听他这样一说,心里更乱了,眼泪纷纷扬扬地往下落,呜咽道:“我才不要孩子呢。”
他大不以为然:“八成已经有了呢。”
她顿足道:“我不要!就是不要!”
他笑着说:“不要小孩子气了,好啦好啦,也不一定呢,抽空去看看医生吧。”
这样的事情令洛美心里十分不舒服,对于看医生则是既想又怕,因为总觉得万一不幸有了的话,容海正的口气似乎是容不得她真的不要的。她现在觉得他是很可怕的,与他作对自己未必占得了上风;而如果真的把孩子生下来,又是件更令人痛心的事——一段毫无感情且随时可能崩溃的婚姻,何苦又牵扯个无辜的小人儿进来?
好在容海正忙得一塌糊涂,对于看医生的事也没有空催促她,洛美好容易等到他晚上回家,他一走出浴室,她便说:“小孩子是最烦人的,你现在这样忙,怕是没空准备当父亲吧。”
他则神色自若地打开了床头灯看文件:“胡说,小孩子是最最可爱的——你去看过医生没有?”
她说:“还没有呢。”
他放下文件,神色淡然地说:“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不年轻了,要个孩子没什么不好的。”
洛美就说:“怎么没什么不好?到时候我们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她一时语塞,虽然两人都心知肚明这段婚姻背后的实质利用关系,但是这种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总不能赤裸裸地直说出来,所以,她叹了口气,说:“‘容太太’这个头衔太沉重,我负荷不了太久。”
他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洛美因为是想存心要设计他的,所以只管将自己的招牌笑容亮出来,甜笑着将他手里的文件拿掉,随手丢到地毯上去,口中说:“人家和你商量正经事,你不要摆出一副大忙人的样子好不好?”
他又“嗯”了一声,才瞧了她一眼,说:“你刚刚扔掉的是公司的一笔两亿四千多万的企划。”
她说:“生意明天再说。”一歪头靠在他胸前,“你怎么这样忙起来了?我成日看不到你。”
容海正好久没有见过她这样小鸟依人的情形,明知她一定是有目的的,可是心里警铃大作,口中却已不自觉地说道:“你想我陪你?那我尽量抽空好了。”
洛美轻轻地说:“不要了,你忙吧。”说着就往后面退,头发拂过他的脸,刷得他鼻子痒痒的,心里也有一种痒痒的感觉,想抓住她的头发来嗅一嗅、吻一吻。
洛美说:“你看你的企划吧,我要睡了。”说着只管拉那被子,一直拉过去了一半,又一圈卷住,像条蛹中的小虫似的,将被子盖到了鼻子,只剩了双眼睛露在外头,眨了两下也闭上了。
容海正说:“你把被子卷去了,我盖什么?”伸手就去拉。
洛美用手揪住了被子,忙睁开眼说:“你现在又不睡。”
他说:“谁说我现在不睡?”将被子拉开了,洛美一张脸已捂得红红的,他望着这张红红的脸,不知不觉间就已低头吻了下去,洛美咯咯一笑,往后躲去,他便一只手扶住了她的脸,还有一只手就去摸灯的开关,手指刚刚触到开关,就听到洛美腻声道:“海正,我不要孩子嘛。”
容海正这个时候“好”字已到了唇边,突然之间明白了她刚才说的是什么话,一刹那间实不亚于一盆凉水兜头泼下,立刻将他拉回了现实。他静静屏息了三秒钟,而后,淡淡地说:“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松开抱她的手,起床去拾了那本企划案就去书房了。
第二天洛美很晚才起床,刚刚打开了房门准备下楼,四姐便上来了:“太太,有位先生一直打电话找您,我没敢吵醒您。”
洛美问:“是谁?”
四姐说:“他说他姓言。”
洛美一怔,想不到言少梓会这样公然将电话打到家里来,忙说:“我在房里听好了。”
果然是言少梓,他开门见山:“我要见你。”
洛美不假思索:“不行。”
他的口气焦灼:“十万火急的事情,你若不愿意与我私下里见面,我们可以约在仰止大厦我的办公室。”
这算是谈公事的保证了,洛美想了一想。他已着急了:“洛美,此事不仅关系着我,对你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你如果不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洛美听他说得这样急迫,于是答应了。换了衣服出门,对四姐说:“先生若问,就说我约了朱医生,今天应诊去了。”
四姐应了声“是”,洛美又说:“不用叫阿川了,我自己开车去。”四姐替她去取了车钥匙来,让司机把车从库中开出来,在台阶下将车交给了洛美。洛美因为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匆匆忙忙地就上了车子,四姐替她关上车门,车子便在蒙蒙细雨中驶出了容宅。
容海正开完了董事会,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孙柏昭正在等他,告诉他说:“已经差不多了。”
两人边说边走回办公室,孙柏昭说:“言少梓果然中计,等他明天悟过来补仓,恐怕江山就换了姓氏了。”
容海正问:“言家的那两个女人呢?”
孙柏昭说:“已经签了股权转让,在这儿。”从手中抽出两份合约给容海正,容海正接过来,又问:“那王静茹呢?”
孙柏昭笑起来:“怕是还在做梦与我们合作呢。”
天罗地网已经撒开,没有一个可以逃掉,收网的绳索紧握在他手中。容海正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可觉察的笑意,忙了这许多天总算要大功告成了。言正杰九泉之下,看到自己精心构筑的企业王国一夕之间溃成瓦砾,想必会气得吐血吧。他的目光移向窗外,仰止广场笼在一片烟雨迷蒙中。
明天,他将立在城市之颠,笑看风雨。
电话响了,是孙柏昭接听,应了一个“是”,便转过身来对他说:“容太太来了,小仙问您有没有空。”
他做了个手势,孙柏昭心领神会,对电话中说:“请容太太过来吧。”而后对他说,“容先生,我先出去了。”
孙柏昭退了出去,恰好在电梯门口遇见了洛美,于是叫了一声“容太太”,洛美却恍若未闻,径直就走过去了,孙柏昭心里奇怪,因为洛美是个极识大体的人,从来不摆什么架子,于是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只见洛美连门都没有敲就进去了,心里就更奇怪了。
容海正将重要的合约文件都放到保险柜里去了,刚刚关上了柜门,拨乱了密码,洛美就已经进来了。
容海正见她脸色苍白,身子在微微地发颤,忙问:“很冷吗?”忙调了暖气,又按铃叫公司的秘书室倒两杯咖啡来,洛美却说:“不用了,我只是来问问你。”
他便说:“问什么?”这才留心到她眼中完全是一种接近崩溃的恐惧,仿佛他是洪水猛兽一样。
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活下来,因为要复仇,要让杀我父亲、妹妹的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容海正,这是你教我的。”
他点头,神色已变成一种淡然的严肃,仿佛已知道她要说什么。
她的身子仍在发着抖,她用一只手撑在桌上,那只手也发着抖,她的声音却软了下来:“海正,我不想了,你收手吧。”
他却笑了:“洛美,我问过你,你拒绝了,现在你却来和我说这个,你说我会不会听?”
洛美却一下子扑到他怀里,低声道:“我求你,海正。”她哀哀地道,“我们可以立刻回千岛湖,也可以去圣·让卡普费拉。你答应过我,要和我在圣·让卡普费拉过一辈子。”
容海正温柔地圈住她,低声道:“我答应你,但要在这件事之后。”
洛美攥着他的衣袖,似乎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固执:“不!我们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他拍拍她的脸颊,“不要小孩子气,这是生意,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更何况,就算你要放过他,我还要算我的账。”
洛美的声音低下去:“可是,我刚刚去见了朱医生。”
这句话立刻吸引了他绝大的注意力,他“嗯”了一声,示意她说下去,她说:“我已经怀孕了。”
他“噢”了一声,看着她:“好消息啊。”
她却是慌乱的,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件事,她说:“请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收手吧。”
他说:“这和孩子有什么关系?”却掩不住心里的高兴,伸手搂住了她,问,“医生说孩子怎么样?男孩还是女孩?”
她仰头看他,眼底的泪光一闪:“才只五十五天,医生说还来得及。”
他不解地问:“来得及做什么?”
她说:“来得及拿掉。”
他的心里一冷,身子也冷了,他望着她,慢慢地告诉她:“你若敢动我的孩子,我绝不会放过你!”
她立刻说:“你收手,我绝不动她。”
他静静地打量他的妻子,像打量一个从未见过的对手,最后,他嗤之以鼻:“你不敢!”
“我敢!”她几乎是本能地叫道,“你不答应我,我立刻去拿掉她。”
他的唇角漾起了一缕笑意,洛美昂着头,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终于不自在起来了:“洛美,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这不是该任性的事。”
“我不是开玩笑,我也不是在任性。”她一字一句地对他说,“容海正,我是来通知你,和你谈判。”
他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了,可是他的口气还是轻松的:“你把咱们的孩子当成一件企划案吗?”
“就算是吧。”她冷冷地说,“你不是想要孩子吗?他应该比你的企划、比你的公司、比你的身家都要重要才对。”
他嘴角一沉:“好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到底是为什么?”
她说:“不为什么。”却不自觉地咬了一下下唇。
容海正示意她坐下来,才说:“我们是盟友,现在你有这样的决定,总是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的。”
洛美烦躁不安,并且更有一种近乎于绝望的口气:“你还想怎么样?我只要求你收手,我甚至肯将孩子生下来。”
他不解地望着她,她自欺欺人地扭过头去,他抓住了她的肩:“官洛美,到底你是什么意思?你看着我!”
她不肯看他,只简单地、生硬地说:“我都知道了。”
不祥的感觉在他心头慢慢扩散,他问:“你知道什么了?”
她垂头不语。
他追问:“你知道什么了?”
她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我知道你的一切阴谋算计!我知道了你的一切卑鄙手段!我知道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完全是个恶魔,而他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孽种!”
他大怒,甩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她唇角迸裂,血渗出来,她既不哭,也不说话,一双深幽幽的大眼睛瞪着他,直瞪到他心里某个部位生生地疼起来。
他木然地转过脸去,冷冷地说:“这一掌是打醒你,让你记清楚,我是你的丈夫,而你维护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你的奸夫!”
她站起来,不言不语,开了门走出去。她走出了宇天大厦、走出了仰止广场……
晚上的时候,雨下大了。城市的雨季,一贯是这种淅淅沥沥的调子,四姐坐在椅子上,揉着她患了关节炎的双腿,心里就在怨这种湿答答的天气。老天似乎刚看了场悲剧,止不住汹涌的泪水纷纷扬扬飘洒下来。
庭院里传来车子的声音,她慌忙站起来出门去,容海正的座车已驶入了穿厅,车窗玻璃降下来,她看见主人那张脸上,有一丝难得的焦急:“太太呢?”
“一大早出去了,说是去看医生了,还没有回来呢。”
容海正示意司机,车子又驶出了容宅。
四姐心中纳闷,刚刚走回客厅,又听到车声,忙又出去,果然是洛美开车回来了,她忙打开车门,说:“先生刚回来找您呢。”正说着,容海正的车子也驶回来了,大约刚刚在门口遇见了,所以掉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