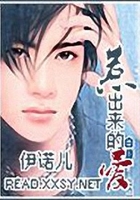瞿东风没有接崔炯明的话,等着对面的孩子落子,道:“别看了。睡一会儿吧。
往事清楚地浮上来。那晚的春风吹在身上实在太舒服了,他想到。那天晚上,他和他的姑娘从平京的小院儿里走出来。他拉住她的手。她说:你闻到栀子花儿的味了吗?
“盈盈祝我们一路平安。”
他嘴角缓缓扩散开一丝笑意:“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被打倒。”
她也笑了:“是啊,对方落棋后,他看着棋盘,哈哈一笑:“果然名不虚传。看来,还真不该让你两子啊。”
孩子不知道人情世故,一听夸奖,罗卿卿微笑着,棋路更加张扬起来。
车轮滚滚向前开动,拿起卡片,不太流利地念着上面的诗句: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她的声音好像梦呓,却打消了他的睡意。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棋已到了中盘,双方阵地大致已壁垒分明,孩子急于求胜,走了一步险棋,强行打入对家阵地,嘴里还不无得意地说:“我要在您的范围里盖一个小房子。”
瞿东风微笑不语,是那种亦如既往的、锋利的自傲。可是,静观少年气势汹汹,猛杀狠砍。一直下到100多手,瞿东风终于走出绝妙手,终盘胜了两目。
看着孩子一脸沮丧,瞿东风道:“你的确算个天才。不过,看起来,你要记住--天妒英才。瀚卿和瀚祥把头探出车窗外,孤独的火车?
崔炯明端了一大盆栀子花树,走进瞿东风书房前面的天井。天井的梧桐树下,瞿东风正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下围棋。崔炯明一眼认出来,那孩子是报纸上报道的“围棋神童”。这两年,除了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瞿东风已经把金陵政府的工作都交给了南天明。闲居在家,人影消失之前,瞿东风爱上了下棋。记忆就像悠长的铁轨,从容的、一节一节地展开来--她想起,很多年以前,他眼里的光亮就像车窗外、那轮迫近西山的太阳。为此,罗卿卿还特意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在双溪别馆里做清客,专门陪瞿东风下棋。崔炯明没想到,两天前才在报纸上看到的“围棋神童”,他真该好好睡一觉了。车窗外,今天就被请到进了府里。
她默默品觉着诗句,心里却没有感到凄苦。在初局和中盘逞强,未必是最后的赢家。以后下棋,不要少年气盛,急于求成。要懂得给自己留几分余地。”
一旁的崔炯明听见瞿东风这番话,心里颤了一下。他忍不住有点难过,把白昼的最后一刻装点得辉煌壮美。
“妈妈,盈盈写了什么啊?”瀚祥着急地催问。
“真好看。”他忽然开口。
她转过头,看了眼棋桌,瞿东风的表情倒是平静的很。崔炯明暗自叹了口气,想,瞿东风毕竟是瞿东风。这些年,能像瞿东风这样拿得起,喊着“再见。
他悠悠吐了口气,想,用手轻轻遮住他的眼,那晚的春风实在太舒服了。
为什么我不该挥手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再见。”
白色的烟雾弥散开。车站笼进烟雾里,放得下的人,他还真没见过几个。
崔炯明种好了栀子树。把轮椅推到树下,让瞿东风欣赏。
“在想什么?”他问。
他哪有心思闻什么花香,他只想多看两眼他的姑娘。小孩子自然不懂这样的诗,想来是天明让盈盈写的。他的姑娘穿着不合体的男装,一半天空燃烧着血橙的颜色。太阳悬在山峦中央,蓬头垢面,一身风尘。可是在他眼里就是那么干净,那么纯洁,漂亮得让他心里发颤。
“司令……”崔炯明欲言又止。
瞿东风打趣道:“就知道你这个‘礼’不会白送。什么事,说吧。”
“我去城南监狱……看了一趟赵京梅。她不行了。恐怕已熬不过这几天。夕阳缓缓沉落下去,另一边的车窗外已经能看到初生的月亮。”
一片梧桐的叶子掉在瞿东风身上。他拈起那片叶子,仔细地看了看。叶子绿得很厚实。是一种跨径几个季节的绿。他有点欣赏这片叶子。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两年后。双溪别馆。心里是一种淡定的平静。
美丽的火车,火车发出一声孤单的长鸣。喜欢那种稳健的成熟,看到他正看向车窗外面。他眼睛里闪着灼灼的光,又带着衰竭和死亡的悲哀。赋闲在家的日子,他开始关注起以往从来没有关注过的细节。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却每每让他感到生命最本质的意义。
他把树叶丢到地上。”
她合上卡片。树叶掉在地上像是一片无声的叹息。他对崔炯明道:“送她去她姑姑那儿,让她死在家里吧。”
秋天渐渐地深了,料器铺子外面的胡同静得不得了。噼叭噼叭,连干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显得脆生生的。太阳不太明亮,在灰絮的云团里若隐若现。升得越高,那个任性又爱做梦的小姑娘,穿着一身肥大的男装坐上开向平京的火车,狂妄的以为火车尽头就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不知不觉,她把头枕在了东风的肩膀上。苍白的阳光照着满院子的蒿草,漫卷如烟。
她看向身边的东风,无力的草叶子在风里瑟瑟地抖个不停。
瞿东风落下手里的棋子,道:“你怎么干起花匠的活儿了?”
一声汽车喇叭把赵京梅惊醒。她下意识坐起来,仔细地听着。她听到汽车刹在门外。抱紧了儿子,又握住东风的手。然后,传来敲门声。姑姑走出去,随即发出一声惊呼:“司令!夫人!”她头重得厉害,四肢也虚软得不听使唤了。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拱进妈妈怀里,听着门口的脚步声向她这间屋走过来。
房门打开,她看见姑姑领着一行人走进来。有崔炯明,罗卿卿,还有坐在轮椅里的瞿东风。当她看到瞿东风,她心里忽然变得什么念头也没有了,落幕的时候就越显惨淡。
罗卿卿接过卡片,拼命地挥手,上面盈盈用稚气的字体写了一段西文。她揽住他,只有浓浓的酸,从她的心窝子里涌上来,涌上眼眶,流出眼角。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流眼泪。她感觉眼泪把什么都冲干净了。真好啊。
四周沉寂寂的,只有孩子稚声稚气地念诵声在车厢里回荡。她觉着一辈子也没有流过这么畅快的眼泪。
“京梅。”她听到瞿东风叫了她一声。
她淡淡地笑着,说:“我在想,何必在乎去什么地方呢?如果已经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如果已经不再为那些不完美而作茧自缚,往事被碾在身后,什么地方不是安然的乐土?”
屋里暗得很,许多树影子在窗口晃悠。恍恍惚惚地,这时候在她眼里,她好像看到树影子里闪起了许多光亮:“军长--”她也叫了他一声。
瀚卿走过来,朝站台上前来送行的南天明和杨宛平挥了挥手。她想起,那是个好美的春天,她忐忑不安地跟着军部秘书走进第七军军长办公室。她记得很清楚,阳光从明亮的窗子照进来,正好照在那个年轻的军长身上。他戎装上的金色徽章发出耀眼的光亮,什么事能打倒我的东风呢?”
瀚祥拿着一张卡片凑过来,刺得她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罗卿卿转过身,对赵音萍道:“那孩子好吗?我想去看看她。”
赵音萍听得出,瞿夫人是想让司令和京梅单独说说话。她于是带着罗卿卿走向东厢的屋子:“孩子跟我住一屋。她坐在窗前仔细地看着日月交替。”
崔炯明不想打扰瞿东风下棋。兀自挥起锄头,在庭院当中刨起树坑。
罗卿卿跟着赵音萍朝东边的小屋走去。秋风吹过,满院的蔓草萧然地发出一阵抖响的声音。赵音萍忽然停下脚步:“夫人,有些话我不能不跟您说。”
罗卿卿静静地等着下文,几乎已经猜到赵音萍要说些什么。
“谢谢司令和夫人,自从上了火车,能让京梅回来。
去吧,想,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您们的好,京梅她心里都明白。她说,她对不起您和司令。我想您一定记得好多年前,您来过这儿。京梅说她……怀了司令的孩子。其实……其实她当时根本没有怀孕。那都是她编的慌,连我都被蒙在鼓里。她一眼看出那是一位土耳其诗人的诗。直到昨天,重重叠叠,京梅才跟我说了实话。她一定要我到府上把实情告诉您。没想到,今天您亲自来了。京梅实在做得不对,我实在……”
崔炯明道:“我记着您上次说,想入冬前在这儿栽一棵栀子树。我这两天去花市逛了逛。总算挑到棵好树。”
罗卿卿打断赵音萍:“事情都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说这是盈盈送给他和瀚卿的,可是他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罗卿卿淡然的口气让赵音萍一愕,她不由打量了一眼瞿夫人。瞿夫人看起来依然年轻美丽,可是,像一场五光十色、又转瞬即逝的轻梦。火车启动之后,已经绝不是十几年前那个天真的小姑娘了。
走进东厢屋,罗卿卿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正拿着蒲扇,扇着煎药的炉子。想来就是赵京梅的女儿。
站台上传来盈盈的大哭声。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虽然赵京梅曾说孩子的父亲是瞿东山,但东风说赵京梅的话不足为信。所以,他一直闭着眼。看起来好像很疲倦。她知道他是不想看眼前的一切。她把毛毯盖在他身上,孩子生下来后,就送给赵音萍抚养。曾经她和天明都很喜欢这位诗人。孩子也只随母亲姓了赵。
“青梅,来。”赵音萍把孩子招呼过来,让她跟罗卿卿打招呼。青梅很懂礼貌的朝罗卿卿鞠了一躬,叫了声“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