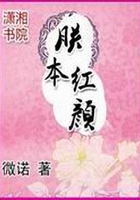靳冬进到老女人家后,就坐在了沙发里。老女人拿出黄药水,还有云南白药开始为他上药。看到她那副细心的模样,一股暖流又涌进了他的心窝,极大地缓解了伤口的疼痛。他眼窝发潮地环视着发空的屋宇,随意地问道:“这么大个房子,几口人住啊?”
她叹口气:“唉,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他似乎一喜,说道:“哦,也空巢了?跟我一样。”
她动容地瞅瞅他,又拿出白纱布来缠他的腿弯。缠完之后,给他沏了一杯热茶,然后坐下了。她自我介绍姓厉,叫厉秋。他暗吃一惊:怎么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秋字啊?真是越来越象了。忽然觉得也应该介绍一下自己了,于是说自己姓靳,叫靳冬。她听了,不知为什么,眼里却掠过一丝惊喜。
闲聊起来不久,他就知道了她每天早上去沙坑边唱歌的原因。自从老闺女出嫁以后,她就越来越觉得心里郁闷,老想跟谁倾诉倾诉,可是跟前又没有可倾诉的人。春天的时候她听说了一句话:放喉唱开怀,去病又消灾。她觉得有道理,自己离江边也近便,所以早上就去江边随便嚎了几嗓子。也别说,嚎过之后,心里真就觉得挺敞亮呢。打那以后她就天天早上都去嚎了。
他夸赞道:“你唱得还挺好听哪。快赶上宋祖英了。真的。”
她自嘲道:“好听啥呀,没把狼吓跑了就不错了。”
他笑道:“亏了没吓跑,不然能到你家来么,还坐在这沙发上?哈哈。”
她也哈哈地笑了。同时又用心地打量了他一眼。
他告辞的时候,她本打算送他到门外就算了,可是见他行走不便,只好搀扶着他亲自送他。他的家比较远,送的时间也比较长。但他们一路走一路唠,并没有感到累乏。进家后,她看见了矮柜上的那个黑框遗像,不由一愣:“咦,她怎么这么象、象”忽然又转而笑道:“哈,她一定是你的老伴了。”
他知道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便点头道:“是的,是的。你俩长得太象了,实在太象了。”她哈哈地笑了。
她见中午马上要到了,就又去厨间帮他做起了饭。望望桌上热腾腾的饭菜,再望望坐在身边笑吟吟的她,他心里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充实和安慰。暗忖,要是天天都这样多好啊。
他夹了一口菜送进嘴里,刚刚咀嚼了一下,就紧皱起眉头:“哎呀,卖咸盐的是不是让你、让你”话说这里又停住了,怕说出来她不高兴。她却主动挑明道:“你是不是说菜做咸了?”他点点头。她说道:“可是咸中有味啊。”
他心里一动,他老伴在世时就常把“咸中有味”挂在嘴边,他经常批驳她。没想到唉,真是太象了,哪儿都象。
他很快就吃完了饭,接下来他就把吃盐过多危害血管的事讲给了她听。还讲了许多不良的生活方式对身体的危害。她听了两眼放光,连连称赞道:“没想到,你的知识这么丰富,我要是早认识你就好了。”在乐于接受别人意见这一点上,他觉得她比他的老伴强多了。
他由于腿上有伤,好几天都没有去成大江,她索性好事做到底,每天都过来给他做饭,而且做出的菜也不再那么猴咸了。还为他洗衣、擦地、端茶、倒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他见了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她清瘦的脸上不时也掠过一阵愉快的笑影。
闲下来时,她还会唱唱老情歌。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敖包相会》。唱到《夫妻双双把家还》时,他都会不失时机地接上董咏唱的那段。清泉似的歌声在屋子里回荡着,俩人显得很开心,都年轻了许多。
他的腿伤好了以后,她不知怎么却又发起烧来。真是按下瓢葫芦起来。她要打电话告诉她的三个儿女们一声,要让他们轮流来照料她。他摆手说:“快别给人家添乱了,你是为了我才感冒的,还是让我来服侍你吧。”
于是,他就又陪着她去医院打点滴。按时让她吃药,还专拣那种无糖的水果买给她吃。她退烧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到江畔小区去了?可是这时却感到一阵子的难舍难离。似乎离开了这个老帅哥她就少了半拉世界。她发现她离不开他了。他太有魅力了。
他看出了她的意思,本想婉拒她,可是她太象他的老伴了。而且不仅相貌上象,名字上象,其它许多地方竟然也很象。曾经有很多人热心地要为他穿针引线,想让他梅开二度,从此远离那份孤独寂寞。他却摇头说:“不找了,心里边有个伴就足够了。”好心人就劝他道:“还是找一个实实惠惠的吧,既可以陪你出去逛街,又可以坐在家里陪你唠喀,有个什么事的时候,还可以相互照应一下。”他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出于对老爸的关心也都劝他找一个吧,可是始终也没让他心旌摇动过。然而眼下他却忽然决定,从此就把她当成他的老伴得了。于是他就挽留她。她见他是真心实意的,就痛快地答应下来。
当下他就把矮柜上的遗像撤掉了,既然已经复活了,还摆它干什么。这一举动的含意,她心领神会。于是就安心地住了下来。这以后,她再也没去江边。一是因为离江边远了来回不方便,二是跟靳冬在一起后心里不郁闷了,所以再去大江就显得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