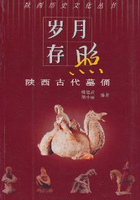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主题是二重复合主题,即全书完整地记录了元魏王朝都洛时期国力以及佛教从鼎盛走向衰亡的全过程,今昔对比,兴衰对比,从而深情婉转地为元魏王朝的命运与佛教盛衰演奏了一曲动人的挽歌,以清丽、感人的文字把元魏王朝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把佛教曾经的繁荣与衰败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将作者的史家笔墨、诗人深情以及曾经亲历的一切传达给后人。
《洛阳伽蓝记》有独特的魅力和多方面的趣味,其反映的社会文化生活是立体、多层次的,既有北魏历史大走向,尤其是北魏后期那繁荣又充满动荡不安的大历史,有记录宏大历史的史家抱负、卓越的叙事才能和语言技巧,并深情地关注一座座佛寺的兴衰,关注市井细民的吃穿住行、喜怒哀乐。对那元魏洛都的一切,作者绵绵追忆,娓娓倾诉,用清丽、平实、动人的语言来叙事、写人、状物,从而把那元魏洛都已渐渐远逝的背影留了下来,让后人继续去感怀,去沉思。作者笔下的元魏洛都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动人,所记录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那么广泛,全书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人文关怀,所展现的元魏洛都社会文化生活图景完全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正如美国学者余国藩评价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史记》是"以文字对抗时间的毁灭性"一样,杨衒之及其《洛阳伽蓝记》也是以作者的追忆与文字,来对抗时间长河对元魏一切人、事、物的毁灭,从而保存了对元魏王朝与佛教的记忆。班固《汉书》评司马迁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也可用来评价杨衒之。
杨衒之眼光博大,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抱负、笔法来叙写元魏洛都的一切,用情婉转、细腻、深厚,行文畅达、清丽,感人至深。杨衒之的为人与思想情趣,我们觉得近于清人评价《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黄叔琳"人之爱其子孙也,何所不至哉!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颜氏家训》的魅力在于"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卢文弨看重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杨衒之深爱元魏,元魏已亡,只有深情回忆,理性反思,婉转倾诉,才能在心底、在文字中让元魏复活。所以,《洛阳伽蓝记》完全可以与古代中国本土的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曹雪芹的《红楼梦》,西方丹纳的《艺术哲学》、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韦尔斯的《人类文明史纲》、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记载广阔而又深细的社会文化生活著作相媲美。
我们先从《洛阳伽蓝记》文本出发,来论证其为二重主题。
一、从《洛阳伽蓝记·序》看《洛阳伽蓝记》主题
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洛阳伽蓝记·序》以叙事为主,兼抒情议论,是全书关乎主题的最重要文字。
先来看看《洛阳伽蓝记·序》前半部分:《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并理在人区,而义兼天外。至于一乘二谛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自项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豪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尔来奔竞,其风遂广。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
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这里追溯了佛教在洛阳古都兴起、发展、繁荣、衰败的经过,记载了从北魏高祖太和十七年(493)建都洛阳,至永熙三年(534)京师迁邺,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的四十余年间的历史。描述了洛都佛寺兴衰两幅画面,倾诉了作者由此引出的浓郁情感,"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交代了《洛阳伽蓝记》写作的动机、意图,并讲明了佛寺取舍的标准以及写作顺序。
作者先从时间角度切入,历时性展开叙述,从长时段来完整回顾了佛教在洛阳兴起与衰败历程:从东汉、西晋、北魏到东魏,即洛阳佛寺在东汉发生、西晋得到发展、北魏繁荣鼎盛而又急剧衰败、东魏已彻底颓败的历程。这样就为叙述元魏洛都王朝与佛事兴衰奠定了动态的时间背景,为浓墨重彩叙写元魏打下了坚实的底子;暗示了北魏作为华夏历史文化继承者的地位,突出元魏都城洛阳是汉魏晋古都的一脉相承,从而与南朝政权争正统,为元魏王朝争得作为华夏文化继承者的地位与自信,表明元魏的政治与文化是上承东汉、西晋的,是一脉相承的。
序言叙述的重点当然是元魏时期即北魏后期,序中完整回忆了迁都洛阳、北魏亡后东魏迁都邺城、东魏武定五年(547)作者重游洛阳旧都的全过程,写前后三个时间段,分别描述了鼎盛与衰败两种景观。从元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开始,到元魏灭亡、东魏迁都邺城结束,完整展现元魏后期的历史。而在这一时期,佛事的兴衰恰与王朝后期的兴衰同步:王朝兴则佛事兴,王朝衰败则佛事衰落。
最盛时,洛阳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这里作者将王朝建筑景观与佛寺建筑景观完全并在一起来写,王朝建筑景观与宗教佛寺景观构成佛、俗二元景观,"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金刹、广殿与灵台、阿房并列,既客观呈现了王朝、佛事繁荣的景象,写出宫殿建筑佛寺建筑共同的富丽,还暗示了王朝与佛事一同鼎盛的局面,从而写出北魏王朝国力、佛事的兴盛,几乎全民崇信佛教,佛教建筑林立富丽,展现元魏宗教的浓厚气氛。这里的叙写都是作者在深情的缅怀中写出的,因为王朝与佛事鼎盛的画面早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只在记忆里,在作者清丽的文字中。
元魏后期,洛阳历经五次浩劫,最惨烈的是第一次,即尔朱荣于528年发动"河阴之变"。尔朱荣诱骗当时执掌朝政的胡太后、少帝和一千三百名王公大臣出城,将其全部屠杀。陈爽《"河阴之变"考论》(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辑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考察,而刘卫东、臧瑞平的《墓志谈"河阴之难"》,则通过造像题记等文物,详细考证死于"河阴之变"的王公贵戚。这些著述都有益于今人体认"河阴之变"的触目惊心与危害。
第二次是元颢入洛阳(约529年),"所统南兵,凌窃市里"。第三次则是尔朱兆攻洛阳(530年),幽禁皇帝于永宁寺,并"扑杀皇子,污辱妃嫔,纵兵虏掠"。第四是高欢(496-547年)以勤王的名义攻打洛阳,杀死尔朱兆。第五次是高欢与孝武帝(532-534年在位)冲突,再次进攻洛阳,孝武帝带随从万余人逃奔关西;高欢于534年立善见为孝静帝(534-549年在位),并迁都邺城,约四十万户洛阳居民同迁至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朝中高官。
历经浩劫的洛阳在孝静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时,"余寺四百二十一所"。至武定五年,作者重览洛阳时,佛寺凋零残破,已是:"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
昔日故都完全颓败,作者将建筑人文景观扩大为三种:代表王朝的人文景观--如城郭、宫室、九逵、双阙,代表佛教的宗教景观--如寺观、庙塔、钟声,以及兼指王朝、宗教与民居景观的墙、巷、荒阶、庭树。作者把三种人文景观连在一块写,这一切都已残败、毁灭,画面广大而悲凉,含蓄表示出王朝与佛寺一同彻底衰亡,于是悲怆抒发"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哀悼王朝与佛事的衰亡。所以作者哀悼的是王朝与佛寺的衰亡,一笔兼写教内、教外两个世界,杨衒之的感怀深沉悲怆而博大,叙佛事也就是写王朝,写王朝也就是叙佛事,二者不可游离;当然也可以说,写佛事是表,叙王朝命运是里,其终极关怀仍可归结为缅怀凭吊王朝之亡,但表与里是不可分离的。
"今日寮廓,钟声罕闻",写尽元魏灭亡后洛都的死寂,没有一点生气与活力,曾经繁荣无比的洛都残破凋零,正如杜甫名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宋代范温曾经以钟声譬喻"韵味":"盖尝闻之撞钟,大音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也。"钟声更多的是记忆里留给人们悠悠不尽的回味。西方史学界在上个世纪诞生了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对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乃至古典文学有不少启迪。年鉴学派著名学者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写有《大地的钟声》一书,关注西方中世纪的教堂钟声,认为"教堂的钟和钟声曾经是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乡村的钟声,先民"曾用今天业已消失的情感系统去倾听,去欣赏它。
这钟声表明了人们与世界,与神圣的另一种关系,表明了人存在于时空并感受时空的另一种方式。解读周围的音响环境也进入了个人和集体身份的构建的过程。钟声构成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慢慢瓦解的交流系统,它有规律地调节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被遗忘的关系方式。它允许人们用各种今天已经消失的形式表达同在的欢腾与喜悦"。所以,钟声曾经寄托了人们的情意,它构成了人们与世界、与神圣的联系,钟声就是一种语言,连接起生者与死者,传达了人们共有的、同在的欢腾与喜悦。所以在《洛阳伽蓝记》中,钟声既代表着佛国曾经的辉煌璀璨,也代表了元魏曾经的繁盛兴旺;但作者在写作时,这钟声仅留在了记忆里,洛都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这样我们更能懂得,作者在正文写永宁寺时,就特别突出,"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