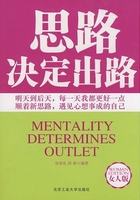惠施离开,庄周和朋友们玩得忘乎所以,唱累了跳,跳累了唱。这帮人来自乡野、市井,来自最底层,而且,其中不少人以卖艺为生,吹拉弹唱,变戏法,耍刀耍枪,埋死人,唱丧歌,一般人不会的他们会,不愿做的事他们做,不屑去的地方他们也去了,从来没见识过的玩意,他们会活灵活现地玩给别人看......妞儿不喜欢,说他们不是正经人,劝庄周不要跟这帮人混在一起。庄周说:"宫里的天地有多大?也就簸箕大罢了;就算做宰相吧,见识有多宽?无非是君王的脸色,手里的那点事;你我的天地有多大?一般人见不到的我们见到了,不知道的也知道了。他们不会在你我跟前说假话,谁也不会蒙谁,比君王整天听好话,恭维的话,假话,自己成了聋子,半聋子;瞎子,半瞎子好得多了。"
妞儿知道劝也没用,任丈夫和他们瞎闹,她只一心抚育才生下几个月的儿子。儿子却生来不结实,三天两头生病,哭闹不止,小脸也缺少血色,妞儿心下焦急。庄周能得仿佛天上的事知一半,地上的事全知,却没办法让孩子健壮起来。
庄周这个破屋子,不断有人来,问字的,求教事的,专门串门来的,不管是谁,是来干什么的,庄周一律盛情接待,有什么招待什么,没什么招待,各自面前一碗粗茶,也能尽兴而归。
这天,来庄周家里的七八个人唱了,跳了,瞎闹了,醉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屋外的草地上。米酒后劲足,从太阳落山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方醒。时候已是仲秋,宋边关夜里很凉。第二天,全都鼻塞,咳嗽、喷嚏连天。庄周和朋友滚在一起,奇怪,他倒没事。
见朋友们感风寒,庄周说:"算了吧,今天不搬家了。"
妞儿说:"我本来就不想搬,人生地不熟,搬去干吗?"
庄周说:"你父亲已经去世,留在这里已经没意思了,不如去个新地界,从头来好一些。"
妞儿想想也是。原来舍不得离开这里,是父亲在;而今父亲殁了,不如离开,免生触景伤情。但仍要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谋生,就太不值了,她说:"夫君,你也看见了,家境如此,无法让孩儿吃得好一些。如果夫君有一官半职,为妻也不至于愁白了头。"
这的确是庄周的难处。而今乱世,正是各国抢人才的时候,若像惠施那样钻头觅缝,不说谋个饭碗,就是进身显赫高官,又有何难?但这样一来,他必须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别人要他怎么说,他只能那样说;要他怎么做,他只能那样做。再也没有自尊,没有自由,这与一件用物何异!
但是,如果依了自己,自己倒是活得自在,可是,他的妞儿,他的儿子,可就苦了,这就叫做要别人的俸禄,就得以自由做代价。庄周有时也自问:"富足与自由能两全吗?"他给自己的回答是:"也许将来有吧,但是,自己怕是享受不到了。"
要庄周谋职的话,妞儿不止说过一次,次次庄周都敷衍、搪塞而过。这回庄周接过孩儿,孩儿瘦得一把骨头,他心里很酸;看看妞儿,妞儿眼里含着泪。庄周说:"庄周惭愧......"
庄周和妞儿之间有怎样的不愉快,外人看不出来,也不关心。庄周的这些朋友只顾租马车的租马车,往车上装破烂的装破烂。一切就绪,让妞儿抱孩子上车。这里是生她养她的土地,每一块地方都稔熟,都难割舍。特别是这里还埋了他的父亲,这一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此诀别也说不定。
马车缓缓移动,妞儿频频回头,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在庄周的眼里,一棵树,远远不只是树,而是天地间的生灵,有它的经历、个性、成长历史,有血有肉;土地,河流,树木,村寨、居民以及各种生灵,都有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无穷无尽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常常为这些别人看来不足为奇的东西激动不已,流连忘返。
庄周少年时候,就从父亲那里知道濮水了。那时,在他眼前就老晃动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垂钓濮水边。父亲说,姜尚垂钓与别人不同,直钩,老钓不上鱼来。他想,这位老人是一位了不得的将帅,周天下开国功臣,算是天下奇人了。想必垂钓未必真的是钓鱼,而是在思谋,在修身养性。濮水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地方。庄周离开楚国,如果不是梦想成为藐姑射山神人,必定去了濮水。
庄周一家三口移居,并没有事先看过居址。反正到处人烟稀少,只要肯出力气,都可以开垦,都可以住人。长长的一条濮河,哪里是当年姜尚垂钓的地方?是一处,还是若干处?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庄周临近这条不算宽大的河,看着夹岸的青山,清幽的河水,河边的青草,被水冲刷得溜光的石头,即喜不自胜。庄周让马车停下,在岸边宽些的地方放下被褥、锅、碗、瓢、盆之类。好友们知道庄周干不了粗活,索性进山,替他砍来木头,割来茅草,花三四天工夫,搭起棚子,可以住人才离开。
庄周很过意不去,一个耍把戏的朋友说:"先生怕我们不来了是吗?我们以天下为家,随时都会来的,我们还要跟你学文墨哩。"
朋友们走了,灾难降临了。马车颠簸几天,还未满周岁的孩子病了,发烧数日不退,后来竟然抽搐不止。死的时候,脸成紫茄色。妞儿又怨又恨,疼痛得如同割了心肝一般,死死地抱住孩子,不肯放下。庄周劝解说:"难为孩子跟我们几个月,受苦几个月,现在他回去了,解脱了,该高兴才是。"
妞儿恨恨地说:"天下没有像你这样的爹。"
庄周说:"他本来是一缕清风,阴阳交合,才有了他,他现在又变成清风了,时时都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不好?"
妞儿骂起来,说:"疯子,你完完全全是个疯子!"
庄周劝解说:"妞儿,放下孩子吧,你老抱着,他如何走得安心?"
妞儿大哭一场,才和丈夫一起,提上锄头,走进林子里,将孩子埋了。按庄周的意思,儿子不是死了,是回到了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无边无缘的空茫世界去了。他或者变成一只飞鸟,或者变成一株树,或者成一块石头,甚至是一阵风。庄周喜欢树,希望儿子变成树。在小小的新坟上,栽了一株小树,命名为合欢。意思很明白,见到这株树,如同见到儿子,彼此高兴。
妞儿失去了儿子,心肝被掏空了,人傻了,呆呆地坐在"合欢树"旁,不肯离去。
新搬来,棚里乱糟糟,日子得重新开始。妞儿心里比这新家还要乱,呆呆地看着,不知道该干什么。庄周第一次把一大摊琐碎而繁难的事揽过来,慢慢地做去。幸而这些朋友帮人帮到底,想得很周到,把床也架起来了。庄周便先铺床,再捡干柴,生火,架锅煮饭,到天黑尽,庄周手脸都变得黑乎乎的时候,饭还是做熟了。
要是儿子还活着,早已哭闹,伸手乱抓了。儿子没了,这点乐趣跟着没了,妞儿想想辛酸,禁不住眼泪又涌了出来。庄周已经完全释然,劝慰妞儿说:"这时候,说不定儿子正玩得高兴呢,他看见你不高兴,他也跟着不高兴了。"
妞儿收住泪,说:"就你会哄我,你就这点本事......"
庄周嬉皮笑脸地说:"为夫要是连这点本事也没有,就不是百无一用,而是一百零一没用了,妞儿还不把为夫赶出家门?"
几天过去,凑凑合合,庄周、妞儿的日子总算平静下来,庄周又想起了那位垂钓江上的大智者,告诉妞儿说:"为夫要像姜尚那样垂钓江上了。"
妞儿跟庄周在一起,耳濡目染,知道不少故事。丈夫说起姜尚,妞儿趁机说:"你就学学那老头子吧,他后来可是武王军师,开国元勋,四代太师。为妻不要求夫君当宰相,当太师,有碗饭吃,有地方住,不怕刮风下雨就行。"
庄周说:"你这要求太容易做到啦,等着吧,先去钓条大鱼回来。"
在宋边关时候用的鱼竿没有带来,还是随意砍了一根小竹子,系上钩,提上笆篓,走出门。别人想不通姜尚为什么用直鱼钩,庄周没有疑问。但他还不能达到钓者之意不在鱼的境界,必须解决燃眉之急--钓上鱼,回去安慰妞儿。
濮水果然水清鱼肥,小半天过去,大大小小居然钓了半笆篓。庄周喜不自胜,往回家的道上走,且歌且行,得意忘形。一阵,有人叫:"钓鱼的,等等!"
庄周回头看时,见是个商人模样的人,却不认识。陌生人说:"呃,看看你钓的鱼!"
庄周想:"今天运气不错,鱼不少,能卖掉一些,换几个钱,买些油盐也好。"这么想着,停下。
陌生人走近,看一眼庄周,说:"啊,原来是庄先生啊?"
庄周不明白在远离睢阳的濮水竟还有人认识他,一面放下笆篓,一面说:"对不起,庄周不认识先生。"
陌生人说:"你忘啦,你管漆园的时候,小人去买过漆。你说割下漆,要如数上交,不卖。小人说,你悄悄卖给我,谁知道?你说,我良心知道。当时,小人很佩服你的,想起来了吗?"
庄周想起来了。那天,这位满脸堆笑的人还说:"良心?良心值几个钱?"
庄周听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他还是不想太便宜了这商人,说:"有良心的人,良心无价;没良心的人,分文不值。本来就没有,如何卖钱?"
这阵,商人说:"我全要了,多少钱?"
庄周说:"无价。"
商人说:"别开玩笑了,几条臭鱼,值几个钱?"
庄周说:"这是我亲自钓上来的,要自己享用。"
商人说:"庄先生,你还是这么固执,这么不开窍,所以,还是这么穷。我告诉你,这一次,小人替宋王出使秦国,发财啦。"
在世人心目中,秦霸,宋无能,庄周的看法也不例外。庄周奇怪宋子偃居然糊涂到让一个商人当使节,去讨好秦国这样丢人的地步,饶有兴趣地问:"说说看,发了多大财?"
商人说:"秦王赐车百辆,庄先生,你没想到吧?"
庄周说:"没想到。以前,秦王长大疮,四处悬赏寻医。能破大疮的赏车一辆;后来秦王长痔疮,许诺只要肯将痔疮舔痊愈,赏车十辆。秦王说了,越往下,奖赏车辆越多。奖赏你一百辆车,你肯定不止舔痔疮了。"
商人一时没醒悟过来,说:"敢向上苍起誓,秦王绝没有让小人舔痔疮,只不过,小人是带了见面礼去的,要不,秦王会这么慷慨......话又说回来,有来有往,也是人之常情。"话说完,才醒悟过来,说,"好你个庄周,你从来都没有忘记挖苦别人,小心你嘴生疔疮。"
庄周说:"是呀,庄某没车奖赏你,生了疮是没人舔的。"想想又添了一句,"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可恨的商人吗?
商人模样的人赶忙分辩说:"谁是商人?本人是御史,姓曹名商。"
庄周长长地"啊"一声,惊得半天没合拢嘴。
庄周回到家,把这件事说给妞儿听,妞儿说:"你那嘴巴呀,积点德行不行?"
庄周正色说:"对这类趋炎附势的跳梁小丑,不刺刺他不知道世间有羞耻二字。"
妞儿说:"这一类人多得很,你能奈何谁?"
庄周说:"为夫谁也奈何不了,但不说我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