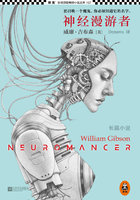一辆马车在狭窄而高低不平的路上行了数日,终于看见一片城堡,又走一阵,到城门前,都尉说:"睢阳到了,你们在车上等我。"
都尉下车,跟城门卫士说了几句,卫士查过都尉腰牌,随即带几个军士出来查看马车上的人和物,都尉说:"车上是末将女儿和女婿,随车之物,不过是吃的穿的。"
军士说:"而今乱世,贼人脑门上也没写个贼字,不可不防。"
都尉说:"末将镇守边关,这道理岂能不知!"
走过三道门,道道都细细盘查,才放都尉、庄周和妞儿入城。这里比楚都城郢小了很多,房屋矮小,建造粗糙,都尉遥指一片略高的房子,说:"那是君侯住地,不可轻易走近,以防不测。"
庄周对这样反复的盘查很不以为然,说:"为政为民,有必要这样畏人如虎?"
都尉说:"你懂啥,宋是小邦,谨慎还经常有人来捣乱呢,不谨慎,还不亡个球蛋!"
都尉带庄周和他的妞儿进一间屋子,见过一个着便服的中年男人,说了几句本地话,这中年男人说:"行,就交给俺啦。"声音嗡嗡的,像堵在鼻子里。
都尉告诉庄周说:"俺妞儿就交给你啦,你要好好待她。"
庄周连连答应说:"一定,请大人放心"。
都尉眼圈发红,回过头对女儿说:"爹回去了,过些日子爹会来瞧你们的。"
妞儿眼泪成串地滴下来,跪在爹面前,说:"爹,别忘了女儿。"
都尉留下些刀币和谷物,中年男人告诉庄周、妞儿说:"你们就暂时住俺这里,再去看看庄先生就职的地方吧。"
庄周只从人们言谈中知道宋,具体情形一无所知。从都尉住地到宋都城睢阳,见到的听到的都与楚相去甚远。什么都粗,住处粗,用的物件粗,连说话也高声大气,老是一副粗嗓子,没有楚地那么文雅。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眼下他什么都不该想。他允诺一定好好待妞儿,不能让她不高兴。
中午,中年男人招待庄周、妞儿吃过午餐,叫来一辆马车,叫庄周、妞儿装上都尉送给他俩的谷物、被褥,坐上,直往都城外行驶。大约行驶一个多时辰,中年男人叫马车停下。这时,出现在庄周眼前的是一片稀疏的树,旁边有幢低矮的小屋。中年男子在屋外叫一声"老头",半天,矮屋里才走出个须发斑白的老人。中年男人说:"收拾一下,回乡养老吧。"
老人央求说:"老爷,你看我管得好好的......"
中年男人不给老人好脸色,说:"这么大一片漆林,每年割下来的漆都不够用,你还有脸说,走吧!"
老人随身带的物件极少,不多工夫,把它们塞进个包袱里,离开了。庄周接替老人职位,将谷物搬进低矮而有恶臭的屋子里。中年男人没进矮屋里,庄周、妞儿再出来的时候,他说:"庄周,这差事不错,要不是都尉来说,轮不到你,好好干,别像老头似的,连这么大块漆园也管不好。要是那样,别怪本官不客气。"
后来,庄周知道这中年人姓郭名浪,少府丞,是少府卿助手,掌管君侯穿衣、吃饭、外出以及用度的官。说官小不算小,大也不算大。在他的印象里,楚地的弓箭、车马、床、柜等等都亮晃晃的好看,他问过人,人说那是上了漆。后来,庄周知道那装在桶里黑乎乎的东西就是漆。这种东西是从漆树上割下来的。这种漆树,楚国随处可见。一定是宋地漆树太少,才栽成一片不说,还得人管着。管就管吧。时建给的刀币早已花光,妞儿爹给的刀币、谷物也不多,不当差,何以糊口?
妞儿可是个喜欢干净的女子,她让庄周帮忙,把矮屋子翻个底朝天,将臭的脏的破烂物件一件件地砸出来,让庄周搬到远处丢掉。搬空了,臭味还浓,妞儿叫庄周抱瓦罐去找水。可这种地方除了下河,没处打水。妞儿见庄周文弱的样子,说:"夫君就别去了,你身子单薄,就算打到水,也拿不回来。"说罢,要去拿大瓦罐。
庄周不肯,说:"你一个柔弱女子,如何能干下河打水这样的粗活?"
妞儿说:"小女子虽说没有本地女子这么牛高马大,却也能耕能织。不然,我和爹吃什么,用什么?如果小女子什么都不能做,你如何养得起?"
庄周说不过妞儿,只好让她下河打水。妞儿一连抱来几瓦罐水,把屋里抹了一遍,地下也冲了,臭味终于没了。好在是秋天气候,还有几分热,到庄周和妞儿一起做熟晚餐的时候,屋里也干了。妞儿在抹过的木板上铺上被褥,就算有个家了。矮屋虽然简陋,却还门窗齐全。这地方离都城远,别说夜间,白天也有野兽出没。开始的时候,妞儿和庄周各睡一头,妞儿听见几声鸟兽的怪叫,怕了,睡到庄周这一头来。妞儿浑身瑟缩,说:"抱俺,俺怕。"
庄周不敢,妞儿就朝庄周怀里拱。庄周触着柔软的身子,浑身不自在起来。但也只是紧紧地抱住妞儿,不敢有非分之想。
一连几天,庄周、妞儿胆壮不少。一天夜里,妞儿在庄周怀里躺一阵,见庄周还只是紧紧地抱住她,她不知道男人是不是都和庄周一样,说:"男人都像你这样吗?"
庄周不解,问:"都像我什么样啊?"
妞儿心头怦怦地剧跳起来,说:"不吃荤腥呀?"
庄周赶忙辩解说:"别的男人吃不吃庄周不知,庄周可是吃的。"
妞儿宁庄周一把,说:"傻蛋!"
妞儿既然把话说开了,胆子也就壮了,索性帮庄周做了一次男女之事。庄周哪曾想男女之事会全身散架般快活,他想:"这辈子是没法离开妞儿了。"一心想进藐姑射山做神仙的庄周第一次尝到做凡人的乐趣。
漆园的事情不算多。妞儿说,园里长满草、小树,漆树长不好,庄周不知道如何是好,妞儿说:"除掉呀!"
庄周说:"好,我和你一起除去吧。"
妞儿又好气又好笑,说:"这么一大片漆树,那么多杂草、小树,俺俩做得了吗,要请人。"
庄周又愁上了,说:"去哪里请呀?"
妞儿说:"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别管,俺去找。"
妞儿出去半天工夫,请来五个农夫,他们裸背赤脚,提砍刀、锄头,进茅草、小树丛里,如入无人之境,劳作十天,一大片漆林杂草与杂树除尽,换了容颜。妞儿按人给了酬劳,农夫们欢天喜地地走了。眼下正是割漆季节,庄周和妞儿每天都要进园里走走看看,怕人偷割,十分辛苦。一天夜里,妞儿睡在庄周身旁,伸手去摸男人胸脯,庄周疼得惊叫起来:"啊啊......"
妞儿说:"你怎么啦?"
庄周说:"天亡我也!"
妞儿惊问:"为啥这样说?"
庄周说:"你摸摸看,我浑身都是这东西。"
妞儿笑岔了气,说:"夫君好傻,这是漆疮,以后你不要进漆园,会慢慢好的。"
妞儿没有再让庄周走进漆园,庄周满身的疙瘩渐渐消下去,没再说"天亡我也"这话,但憋了许多日子没敢挨妞儿的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