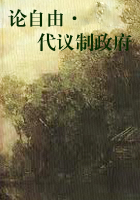我们决定接受克什米尔的加入并用飞机运送军队到那里去,但我们有一个条件,当克什米尔的和平与秩序建立起来之后,该加入将必须由克什米尔人民来加以判定。在当前的危机时刻,而且克什米尔人民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我们并不急于了断任何事情。唯有他们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我们已经宣布,克什米尔的命运将最终由当地人民来决定。我们已经对克什米尔人民和世界做了那项保证,而且哈里·辛格大君也对此予以支持。我们将不会也不能收回该项承诺。当和平与秩序建立之后,我们准备在联合国之类的国际保护下举行公民投票。我们希望,对人民而言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公民投票,并且我们将接受他们的裁决。我不能想象出有比这更公平和公正的建议了。Lakhanpal, PL, Essential Documents and Notes on Kashmir Dispute, Delhi: International Books, 1965, p72
巴基斯坦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缔结了《保持原状协定》。有学者据此认为:“根据这项协定,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承担了从前英王政府或者分治以前印度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克什米尔除了巴基斯坦以外不同其他国家建立任何关系;负有加入巴基斯坦的义务。这就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一事成为无效。”G阿拉纳着,《伟大的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袁维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2-423页。其实,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的《保持原状协定》只谈及继续保持双方的既有关系,并没有涉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归属。此外,克什米尔政府当时还打算与印度缔结相同的协定,只是因为印度的狡黠而未果。倘若印度当时爽快地与克什米尔签订了《保持原状协定》,那岂不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也加入印度了?所以,不能以签署《保持原状协定》为依据来否定《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
1947年10月24日,克什米尔反叛的穆斯林部落民建立了自由克什米尔政府。阿拉斯太尔·兰姆据此质问:“1947年10月26日,哈里·辛格大君正式加入印度,他把自由克什米尔包括在内吗,即便是从理论上讲的加入?”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 154国家的诞生与消灭通常被看作国内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的问题。
人们公认,一个新国家是否已经出现或一个旧国家是否不再存在的问题,应以国际法为根据来解答。国际法的有关原则被陈述如下:如果一个独立政府对一定领土发布强制命令而成立以及如果该政府是有效的话,即该政府有能力获得居住在该地区中的人对这一命令持久的服从,那么国际法意义上的新国家就已出现[美]凯尔森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由于自由克什米尔政府从此开始,就持久地使该地区的人民服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说,哈里·辛格大君及其后续者的政令自那以后就不能再在自由克什米尔地区实行。因此,从此之后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就不再是以前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是一个分裂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
国家的疆界理应由国际条约来决定。如果没有相关各国的协定,那么一国领土为另一国所占有,就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使各国负有尊重相互间的领土完整的责任。对国际法的违反引起的后果是:权利受非法占领所侵犯的国家,有权对要为这一侵犯负责的那个国家诉诸战争或报复上引书,第239页。因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没能独立,而是被迫地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并且,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遭到分裂,分别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着,只有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才能最终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定位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印度和巴基斯坦缔约加以解决,而非单方面就能确定它的永久地位。
克什米尔问题做为一个错综复杂的争端,它的法律背景极为模糊含混。根据前文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哈里·辛格大君签署《加入证书》并无具体的法律依据,他只是基于传统和当时通行的作法行事而已。也就是说,克什米尔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应对它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而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展开评论。正如前文所阐明的那样,英印帝国里的500多个印度土邦虽然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是穆斯林,印度最后吞并了那些位于其境内的穆斯林作统治者的土邦。尼赫鲁自己也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其他印度土邦相提并论。1952年8月7日,他在印度议会讲话中说: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7年10月已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彻底地加入印度了。这是明白无误而不可辩驳的,因为每个印度土邦都是依据这样的条款在那年的9月或稍后完成加入程序。难道人们就能够说,因为它们的加入仅仅限于三个方面,所以每个土邦的加入都是不彻底的?当然不能这样说。它们的加入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彻底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10月底的加入也是这样,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彻底的。Information Service of India, Kashmir, 1947-56: Excerpts from Prime Minister Nehrus Speeches, New Delhi, 1956, p35
尼赫鲁这种比较方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承认,印度在与巴基斯坦争夺印度土邦的问题上,无疑实行了双重标准:对于穆斯林做土邦主的朱纳加德、海德拉巴等土邦的归属,认为应该由人民意志来决定,最后用武力强行改变了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对于印度教徒做土邦主的克什米尔,则坚持《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并用武力维持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就无怪乎巴基斯坦前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会说:“印度对克什米尔采取的行动与在朱纳加德、海德拉巴的如出一辙,它完全缺乏任何道德基础,而仅仅是建立在通常的‘强权即真理’的帝国主义准则的基础上。
”Mohamad Ali, All Parties conference of Kashmir, 1955: opening speech by the Honble Mr Mohamad Ali, Karachi : Ferozsons, 1955, p20因此,如果要坚持哈里·辛格大君签署的《加入证书》具有法律效力,那应该如何看待印度对朱纳加德的土邦主所采取的相同措施呢?难怪会有学者坚持认为:“从法律上说,朱纳加德土邦仍然是被印度占领的巴基斯坦的领土。”Mushtaqur Rahman, Divided Kashmi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i peopl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65
此外,印度不仅仅在土邦问题上采取以我为中心的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亦复如此。卡?古普塔说:“尼赫鲁总是拒绝让克什米尔问题听命于国际仲裁。可是,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同意将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印]卡?古普塔着,《中印边界秘史》,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228页。可见印度是将自己的实力地位作为处理领土问题的基础。在与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时,印度也总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献资料作为谈判的既定法律基础,最典型的就是它在阿克赛钦和“麦克马洪线”上的立场。中印边界争端总共分为三段,主要集中在西段的阿克赛钦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印度认为,查谟政府和西藏地区当局在1842年签订的条约,划定了两地之间的边界,据此阿克赛钦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但是,从本文第一章所翻译的该协议全文内容来看,实际的情况是:
这个条约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将维持原状,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没有关于边界具体位置的任何规定或暗示。……而且,这个条约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争论的地区,绝大部分(约占80%)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约的中国的新疆。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约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经不属于新疆而属于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经建议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结果。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以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59年12月26日)》,《中印边界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2页。
查谟与西藏在国际上作为两个不具有国家主权的地方政府,它们之间签订的条约不能引以为国际边界划定之凭据,何况条约根本未涉及此一问题。印度政府还认为,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印政府、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共同参加的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产生的,因此是有效的。但实际情况是:
当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陈贻范,不但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且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训令,在1914年7月3日正式向会议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驻英国公使刘玉麟,又在同年7月3日和7日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这个立场。……事实上,在西姆拉会议上只讨论过中国西藏地方同中国其他部分以及所谓内外藏的界线,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和印度的边界。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代表和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在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根本没有通知中国,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上过西姆拉会议的日程。上引,第34页。
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西姆拉协议》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更遑论因它而衍生出来的英印帝国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私相授受的“麦克马洪线”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所持的立场,与它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如出一辙。
基于上述的对比分析,关于哈里·辛格大君签署《加入证书》标志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一劳永逸地加入印度的主张就要大打折扣。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举行公民投票作最后的决定,这也是印度早期的主张。在克什米尔争端的最初几年里,印度一直坚持通过公民投票来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它与谢赫·阿卜杜拉的关系还很好,自信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赢得克什米尔。但在1953年与谢赫·阿卜杜拉的关系破裂之后,印度再无通过公民投票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自信心了,因此态度来了个完全的逆转。
1965年,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坦率地承认,“克什米尔将投票加入巴基斯坦,我们将会失去它。”Mushtaqur Rahman, Divided Kashmi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i peopl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p103有了1947年西北边境省和锡尔赫特县的例子,这两个地区开始都是国大党占据优势,但在最后一刻公民投票加入巴基斯坦,印度再也不敢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举行公民投票了。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道德是隐性的法律,法律是显性的道德。” 此言极是!不以道德为依归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更多的是霸权主义的体现。就其本质而言,法律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而已,就如洛林所阐明的那样:“在现实中,每项法律规范对应着一条演进中的道德准则。在法律规范继起之后,它倾向于使道德准则得到普遍的遵从。所有的法律规范在实现目的之后就会消失,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将随之消亡。”罗斯科?庞德着,《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人们常说“恶法非法”,既然良法才是法,则法律与道德庶几无异矣。因为法律从属于道德,所以,即使在承认哈里·辛格大君有权签署《加入证书》的情况下,印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诉求也由于它对相同的问题采用双重标准而遭人质疑。也就是说,从狭义的法律来讲,哈里·辛格大君有权签署《加入证书》;但就广义的法律而言,这份《加入证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可以推论出,把印巴两国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争夺看作一个法律争端,这种观点显得过于单纯。